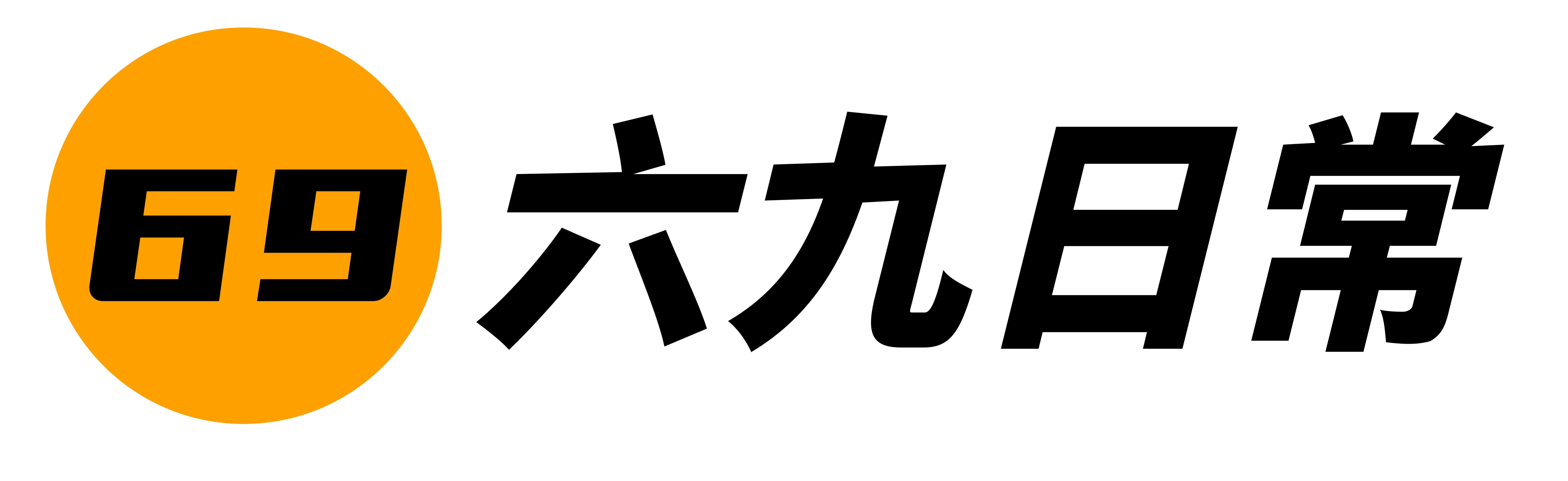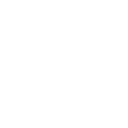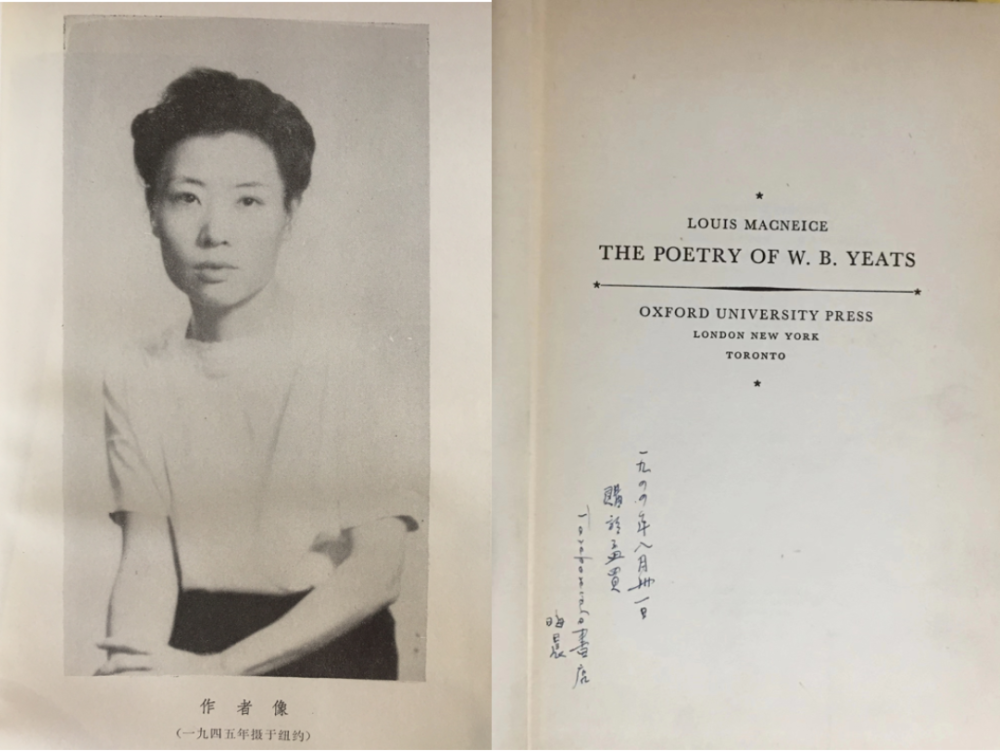
著名记者杨刚(1905-1957)和她在《叶芝诗论》一书扉页上的签名。
2021年夏天,起念细读一读叶芝的诗,遂将叶芝的传记、相关研究,连同诗集注本,搜罗了不少。可惜,这个计划尚未施行就搁置了。2023年岁末,友人写就一部讲叶芝的大著,嘱为校阅,乃将这些蒙尘的书重找出来,略加检视。
其中有一册是大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著作《叶芝诗论》(The Poetry of W.B.Yeats),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书名页写有三行蓝色钢笔字“一九四四年八月卅一日购于孟买Tajaposevala书店”,后署“晦晨”两个字。
初购时,未暇留意“晦晨”为谁何。其实,只需上网一搜,就能知道这是有名的记者杨刚女士用过的笔名,1984年出版的《杨刚文集》里即收入一首题为《晦晨》的诗,写于1940年。杨刚的笔名很多——事实上,“杨刚”也是笔名,她原名杨季徵,29岁时出版的译著——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则署名“杨缤”,“杨缤”是她自就读燕京大学就用开了的一个名字。
《杨刚文集》附录胡绳、袁水拍的《追忆杨刚》一文,笔调近于官方定论,然公众对杨刚的认知亦往往同此,故将记述生平的一段节引如下:
杨刚同志在三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她协助埃德加·斯诺编译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介绍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品到国外去。她为报纸写国内外通讯、报告文学、社论,主编文艺副刊。在四十年代的新闻战线、文艺战线上留下了显著的业绩。她还在重庆、香港、美国的复杂艰难的环境里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事工作。她结识了史沫特莱等英美记者和学者,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她先后在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对外事务与宣传工作,曾任周总理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她生前为周恩来同志所倚重,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杨刚同志逝世后很久,还惋惜她过早去世,曾关心地向龚澎同志了解杨刚的情况,说杨刚是他所器重的女干部之一。
杨刚去美国的经历,一般文献皆简短记述“1944年夏赴美留学,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而已。《费正清自传》(Chinabound)里倒记下了原委:杨刚去留学,是费正清帮她申请到了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奖学金,费正清在外交部的友人也出了力,杨刚在燕京大学时往还最多的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亦予支持。“她的出国护照多亏《大公报》发行人胡霖帮忙,才终于拿到手”(《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第339页)。但假若在孟买的书店里买下《叶芝诗论》的那个人就是杨刚,该如何解释她1944年8月不在美国而在印度的事实呢?
原来,杨刚是从战时的重庆转道印度,之后才乘船去美的。关于杨刚在印度的踪迹,也有旁证。1945年6月12日,金克木从加尔各答致信沈从文,里头有这样一句:“树臧兄消息闻之甚为欣慰,前杨刚过印时已曾言矣……”(《风烛灰》附录)所谓“杨刚过印”,当指1944年杨刚途经印度。还有一段叙述,格外生动,出自赵萝蕤《杨刚二三事》。这篇文字刊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八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此后几种赵萝蕤的文集均未收入,读者想来不多。赵萝蕤与杨刚,乃燕京大学旧识,《杨刚二三事》记二人重遇:
我们再次见面却很意外,那是一九四四年秋在印度孟买的大街上。久别重逢,格外亲热。她熟识一位印度女记者。在我们候船去美国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在一起,一同谈天,还看了许多印度的民间歌舞。我们也访问了孟买印度共产党的总部(书记是约希同志)。好像这是个有三层楼的大四合院,住着许多同志。我们上楼盘膝而坐,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手抓饭。我们从孟买同船去美国,航程十八天,路上杨缤的兴致一直很高,常常赋诗言志,并嘱我以后要给《大公报》投稿。
赵萝蕤当时与丈夫陈梦家同行。二人于1944年9月16日从昆明飞往加尔各答。《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称:“据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档案所存1944年11月24日赵萝蕤致威尔森函……他们在加尔各答待了10天,在孟买度过了18天。”(《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撰,中华书局2021年8月第一版,第176页)这样推算起来,杨刚、赵萝蕤、陈梦家等人大约是在1944年10月15日从孟买上船赴美的。在那册《叶芝诗论》里夹带了一份油印英文小报,名为The Mitchell Pacifier,日期为1944年10月26日。稍稍查检,原来这是二战后期服役的美国军舰“威廉・米切尔将军号”(USS General William Mitchell)上发行的一种小报,刊载当时全球战况。据记载,“威廉・米切尔将军号”于1944年10月7日停靠孟买,11月17日最终泊于加州圣迭戈。杨刚一行很可能就是搭乘这艘军舰到美国的。赵萝蕤称航程共十八天,则他们是11月初才抵达美国。这份10月26日的小报,应该是杨刚在船上读了之后随便夹进自己的书里的。
关于杨刚初到美国时的情形,最有价值的中文文献是萧乾写的《杨刚与包贵思》(见《杨刚文集》附录)。文章译引了一些杨刚写给包贵思的信,时间集中在1945年2月到10月间。其中写于2月12日的一封信,杨刚记述了在拉德克里夫学院就读的情形,尤其是谈到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
我已经在五号注册了,选了小说、批评、一八〇〇年以来的抒情诗以及德语。其实,我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抒情诗还算是较接近我的理想。我不想拿学位,拉德克里夫学院当局也已同意了。只有德语一课我是正式生,其他几门都是旁听。这个学期三月五日开学。我还参加“亨利·詹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我以后也许放弃德语,因为太占时间,也太枯燥。我同时还得给《大公报》写稿,要看许多报刊,访问许多人。我对了解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很感兴趣。六月里我得找点零活儿干,因为我的收入不够我维持学业的。我既然不拿学位,申请奖学金就有困难。另外,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镜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这段文字暴露了杨刚在文学研究上的企图心:“其实,我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而她选的两门课——文学批评和一八〇〇年以来的抒情诗——其实都能跟她在孟买购下的那册《叶芝诗论》联系起来:麦克尼斯的著作是文学批评,而叶芝的诗当然属于“一八〇〇年以来的抒情诗”。我们可以蛮有把握地说,《叶芝诗论》不是那种于旅次随手买下的读物,而是能体现杨刚文学志趣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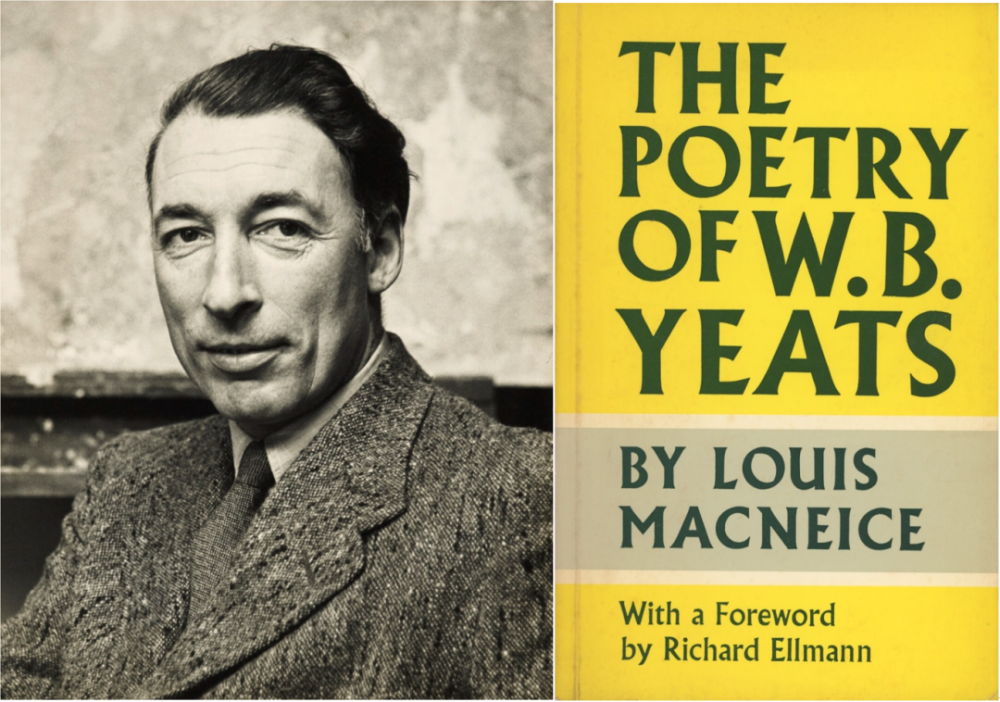
英国诗人麦克尼斯(1907-1963)和他的《叶芝诗论》。
《叶芝诗论》上从头到尾有多处橘黄色铅笔画线,我猜是杨刚阅读时留下的。其中一处,或许是她读了心有戚戚焉者。麦克尼斯指出,叶芝的诗题材范围相对窄,诗人对那些大的话题,什么普遍的知识啦,普适理想啦,世界大同啦,都很反感。叶芝提出的问题也许简单的,但绝非如一些看轻他的论者所以为的那样是琐屑的,“除非认为,一个人若是生活在落后的国家,觉得别的国家的先进思想并不餍心切理,那他就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了。也许叶芝的种种局限令他没能写出最伟大的那类诗,但却使他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可能是最好的诗。”(原书第19页)
杨刚之前生活在落后的国家,现在她到了美国,“对了解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很感兴趣”。然而,待了四年之后,她终竟觉得这个国家的思想并不餍心切理,还是怀着理想,选择回到了中国,拥抱那未卜的前程。反复翻阅《叶芝诗论》,最感好奇的是,在孟买那夏秋之际,38岁的杨刚是否正处于命运的小径的某个分岔点上:朝一边走,她可以研究文学,赋诗谈艺,朝另一边走,她将投身革命洪流……还是说,前一种选择,其实本就没有充分展开的可能,而只是那极特殊的历史时空罅隙中的一道光亮而已?
刘铮
刘小磊
结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