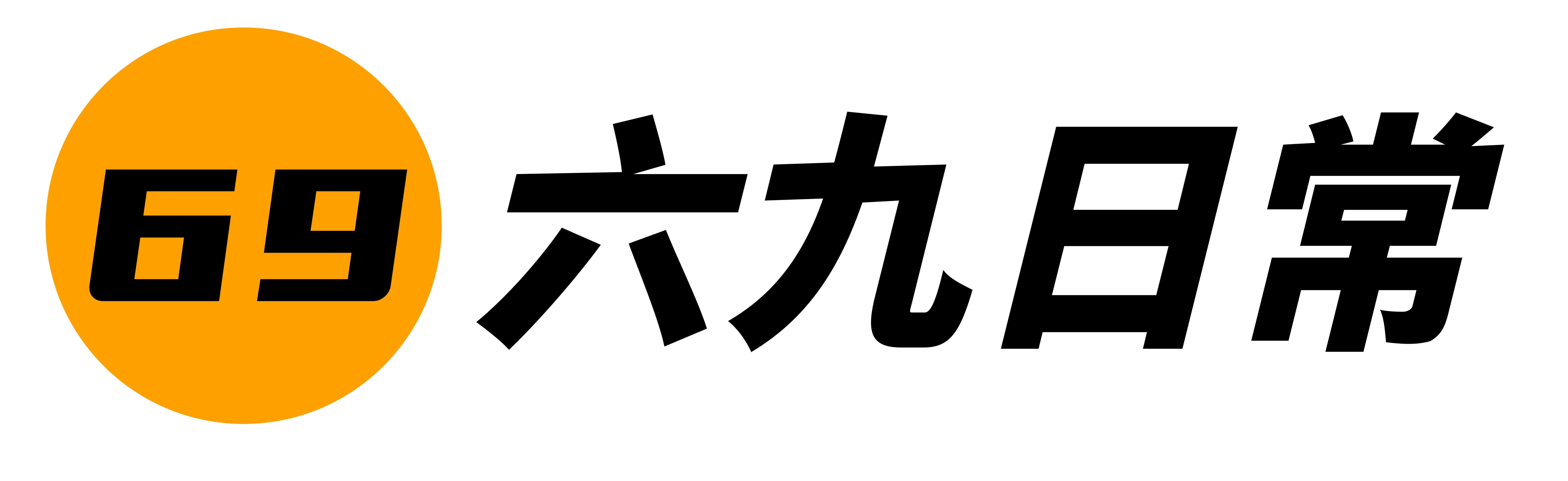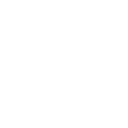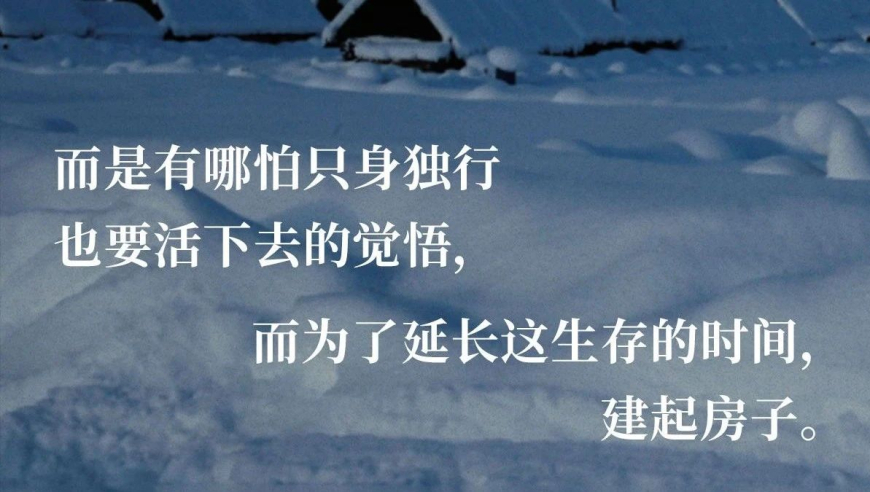歌剧《凯撒》在香港艺术节首演结束第二天,两位主演几乎脚不沾地。吴兴国和当代传奇剧场成员一早便飞回台湾工作,张军也准备下午返程,翌日是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正式开学日,他身为校长,得给全校开大会。
疫情三年延宕下来,分隔两岸的主演几乎要放弃这台戏。香港艺术节总监苏国云一直鼓励他们。2023年年中,大家终于下定决心做戏。苏国云趁热打铁,还未开始排练,便建议先确定演出日期。张军形容,这部戏是“被倒逼”出来的。
线下排练只有三次。前两次吴兴国来上海分别待了12天,然后便是抵达香港后的一周排演。在上海的学校会议室里,吴兴国拿着剧本、乐谱调整表演,张军则进进出出,在排戏与开会间无缝衔接。更多时候是隔空排练,除了两位主演,其他演员、舞美、剧场空间,到开演前三天,才真正组合起来。
制作人、编舞林秀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段时间,许多电影片方邀约吴兴国,除去在《封神》彩蛋中的短暂露脸(饰演闻仲),他都拒绝了,为的是留时间排这个戏。
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写下距今两千多年的凯撒故事。戏剧虽以凯撒为名,真正的主角却并非凯撒,而是在元老怂恿下刺杀凯撒的卜拓思,他最终因各元老互相猜忌及杀戮而自招恶果。

吴兴国(中)和张军(右)在歌剧《凯撒》舞台上。受访者供图
当代传奇剧场版《凯撒》于2024年2月下旬上演,由旅法作曲家许舒亚以歌剧形式作曲,戏曲出身的吴兴国和张军,用京昆唱腔演绎。
舞台上,凯撒身披古罗马时期的黄金铠甲,足下却着厚底鞋,发怒时,“啪”地甩出水袖。歌队仪式性的动作带有现代舞的痕迹,实时投影手法也加入戏中。

吴兴国在《凯撒》中饰演凯撒的造型。受访者供图
100分钟里,吴兴国和张军两人不断转换角色,时而是讨论刺杀凯撒的元老贾修司和卜拓思,时而是凯撒和预言死亡的先知。戏曲行当在二人举手投足间浮现,吴兴国的表演混合了老生、武生、花脸、丑角,张军饰演卜拓思时,则突破一贯文小生形象,以武小生亮相。

张军在《凯撒》中饰演的先知。受访者供图
对于演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音乐。“希腊时代就是拿一个像我们的大阮一样的弹的(乐器)这样唱的,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古朴简单的一种旋律,但实际上他做得很复杂。”吴兴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张军被两大段独唱“搞得极其崩溃”。戏曲有两样东西与歌剧截然不同,一是主奏的乐器,如京剧的京胡、昆曲的笛子,都会跟着唱腔走,二是所有乐器产生的音乐织体是与唱腔和谐的。而《凯撒》的衬底音乐,难以听出主旋律,唯有靠死记硬背。
安东尼在凯撒葬礼上的演讲段落堪称全剧华彩,谱成唱段后,吴兴国犯了难,如果全部用唱的,他觉得过长,可又希望保留完整,最终决定,唱一段,重复一句相同的台词。
“我一唱这段就非常害怕。我连睡觉做梦,都在背这一段。”真正练起来,吴兴国才发现这样处理的难度。歌剧的念白镶嵌在间奏里,在他说那句话时,需要咬合两个八拍小节音乐,不是真的在唱,但是形同唱。
两位戏曲演员都不是第一次演出歌剧。2006年,吴兴国和多明戈合作,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张艺谋执导、谭盾作曲的歌剧《秦始皇》。2008年,谭盾为荷兰皇家歌剧院演出的《马可·波罗》作曲,邀请张军用昆曲唱腔演绎。
分别活跃在台湾京剧界与上海昆曲界的两人,在戏曲传承上,不谋而合地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安分”的路。
出走
1986年,吴兴国33岁,和妻子林秀伟携手创立了民间剧团“当代传奇剧场”。他们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欲望城国》,作为创团戏,在台北首演。戏以京剧为底子,融入话剧、现代舞乃至嘻哈等元素,奠定了当代传奇剧场的作品气质。这一年,12岁的张军进入上海戏校昆三班学习。
如果说,《欲望城国》基本上还是类似于大陆《曹操与杨修》的现代京剧,2001年创作的《李尔在此》则完全打破了京剧的完整形式,只借用了京剧的某些表演技法,利用分饰多角甚至模糊角色与演员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特殊美学。
之后,吴兴国将目光由莎剧投向了更广阔的西方经典,京剧元素也以更隐蔽、灵活的形式出现在剧场里。改编自贝克特《等待戈多》的《等待果陀》,几乎接近一部话剧。戏曲出身的演员们,自由游弋于京昆、相声、吟唱、写实表演之间。两个流浪汉,一个念京白,一个念韵白,时有吟唱或锣鼓经的节奏暗藏其中。

当代传奇剧场版《等待果陀》(又译《等待戈多》)剧照。资料图
《李尔在此》诞生15年后,张军带着向吴兴国致敬的意味,做了独角戏昆曲《我,哈姆雷特》。后来,他把这个剧目带到了大英博物馆。闭馆后,两三百名欧洲观众坐在33号厅,中国乐器次第摆开,张军一人分饰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掘墓人四个角色,涵盖了生、旦、末、丑行当,文言文、白话文、英语来回切换。
2009年,张军辞去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的职位,成立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大部分圈内人都不看好他的选择,在这个资源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家院团的行业里,“个体户”的困难可想而知,有的人甚至担心,他会最终因生存问题放弃昆曲。
张军只一心想把“一些天马行空的事情”做成。在当时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鼓励有条件的名角自己成立团队,但如何经营剧团,全靠他自己摸索。“成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干嘛。国有的院团都生存艰难,更别说私营院团。但我只有一个办法入手,就是把我想做的戏呈现出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歌剧之后,他与谭盾再度合作,两人跑到上海朱家角一个荒废的园子里待了半年,经过蚊群与雨水的洗礼后,推出园林实景版《牡丹亭》。这出戏14年来一直活着,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演出。四百多年前,文人士大夫月夜赏戏的风雅与趣味,观众于园林中得以窥见。
所谓戏曲,曲占一半。张军和吴兴国在音乐方面的探索颇多。
张军与音乐家彭程合作“水磨新调”,在保留昆曲传统音乐、唱词和唱腔的基础上,将昆曲的“水磨腔”与当今世界音乐风格相融合,包含了新世纪、电音、摇滚、爵士等风格迥异的音乐元素。

张军(右)曾尝试昆曲与爵士乐融合,图为2008年6月,他与比利时钢琴家尚·马龙(左)在赈灾义演音乐会的记者会上合作。视觉中国
2018年,张军在张学友刚开过演唱会的场馆,举办了一场“水磨新调”新昆曲万人演唱会。台上的张军潸然泪下——上一次万人共享昆曲艺术的历史记载,应该追溯到至少两百年前的中秋节虎丘曲会。在演后的录像里,他看到来了许多传统的昆曲观众,也吸引了“完全不一样的、无法想象的观众阶层”。
张军通过与各种艺术门类的跨界合作来拓展昆曲传播的渠道,先后同音乐家谭盾、指挥家汤沐海、日本歌舞伎演员市川笑也、英国小提琴家Charlie Siem、美国爵士大师Bobby McFerrin等艺术家跨界合作。
2007年,吴兴国与音乐人周华健、作家张大春合作,为年轻人打造了一台摇滚京剧《水浒108》,年轻人演,年轻人看。到《仲夏夜之梦》,有了之前摇滚京剧的经验,音乐旋律更加活泼,吴兴国起用了纽约大学专攻电影音乐的年轻音乐家,打造出一台颇具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
吴兴国曾问学生们,吉他和锣鼓,你们更喜欢哪个?学生们笑而不答。吴兴国感到一种尴尬与说不出的微妙:虽然他们出身京剧,应是喜欢传统的,但身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是喜欢摇滚。
危机感
大学毕业后,吴兴国加入“陆光国剧队”,拜台湾四大老生之一周正荣为师。1980年代,随着经济起飞和老兵退伍,国民党入台之后一手扶持的戏曲已失去昔日荣光。吴兴国所在的军中剧团,没有经费压力,但也是惨淡经营。他看见老师在舞台上唱戏时,台下吵闹声把他的声音都盖过,可老师充耳不闻,继续往下演。
头,磕过了,技艺,长在身上。吴兴国想的是,创立一个新的剧团。演传统戏生存不了,那可以结合在大学里读到的莎士比亚、希腊悲剧、西方现代文学吗?可以直接借着莎士比亚的平台跳到世界,给国际观众看吗?
海峡两岸的情形相差无几。1994年,张军毕业正式进入上海昆剧团工作,面临的是无戏可演,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全国红红火火的经济建设中,人们似乎顾不上欣赏传统文化,昆曲受到很大冲击。演出的时候,台上演员三十几个,开演后拉开幕布,发现台下观众只有几个,目睹如此情境的张军几乎感到绝望。
当时,张军与同学成立了一个流行组合,最终,他放弃签约当歌星的机会,留下来唱戏。1999年,参演35折《牡丹亭》的经历,打开了张军对昆曲传承与发展的新视角。
为他们录制现场演出的摄像师,经常在录了15分钟后睡着,摄像机倒下,导播就在耳机里骂:“你怎么又睡着了!”但那次演出的摄像师却对张军说,你们这个戏,越来越精彩。
演到《闹殇》这一折,杜丽娘的葬礼热闹非常,几十个演员披麻戴孝走入观众席撒纸钱,把出殡的东西放到广场上去烧掉。民俗入昆曲,这对于当时的艺术观念来说,几乎不可想象。作为一个年轻戏曲演员,张军忽然发现,原来戏可以这样,而不非得像自己所受的传统戏曲教育里划定的样子。
“如果观众都不喜欢,你能坚持下去吗?你说这个行业里的人耐得住清贫和寂寞,那不是一句空话,还得让这些人内心充满了能量,才能够走下去。”张军直言。
在《凯撒》中,吴兴国以韵白和京白交错说着台词。这样的表演方式在早期演绎莎剧时便形成了。他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念白的抒情性,需要用韵白表现,但又希望现代观众在不看字幕的情况下听得更清楚,因此穿插一些京白。
2001年,《欲望城国》来到北大的百年讲堂演出,两千多个座位虽未坐满,演出结束后,上百名观众围到舞台前,争先恐后地提问。当时,吴兴国也是用韵白京白穿插表演,没有人觉得他很怪,有的大学生甚至说,京剧为什么不都这样演,这样演的话,我就更爱了。

吴兴国(右)在根据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改编的戏剧《欲望城国》中。资料图
吴兴国始终有一种危机感:“知识爆炸时代,当你的语言别人不懂的时候,他就进不去,尽管他认为你很细致,很美,很有创造性。”因为观众在变,由纯粹的欣赏传统戏曲,变为同时接受电影、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影响。
为了吸引新的观众走入剧场,吴兴国选择的是一条“跨文化剧场”的道路,从西方戏剧经典中取材改编,同时融入京剧表演程式、东方美学思想。在当代传奇剧场的观众中,大致四分之三的人,是接触各种艺术品类的文艺爱好者。
创办民间剧团,固然要承受更大的生存压力,但胜在没精神包袱。吴兴国理解一些传统剧团的为难,定位为“继承传统”的他们,若想创新,未必能够走得很远。“我们正好是一个民间团队,我也是希望,帮传统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尽量去开发它。”
本质的,当代的
这些年,大陆戏曲院团创新剧目不断,张军观察下来,发现成功的不多。在他的标准里,上乘之作,能够同时凸显三件事:剧种的独特性,戏的精神内核,还有舞台上的演员。
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第一百场的表演后,张军深受震撼,“就是一个字,雅。一个很雅的审美,一个很雅的戏台上,一群很雅的人在那里演”。而“雅”正是昆剧的本质特征。年轻演员们彼此磨合了一百场,在台上非常难得地松弛到极致。当下他还悟出一件事情:昆曲最伟大的样式,就是不使劲,但又不是没戏,而是信手拈来。

2024年3月14日下午,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在台湾高雄演举办公开彩排。视觉中国
然而,更多的新戏只是昙花一现,遑论打磨。“有的时候源头上可能没有找到三合一的默契度,硬要去用昆曲演一个所谓的什么戏,事实证明不成功,只能马放南山了。”
张军有时担任评委,会告诫自己的学弟学妹,要经得住诱惑,假如有人请他演《梁祝》,他肯定不演,因为知道比不过越剧里“死去活来的那种缠绵”。京剧演帝王将相,沪剧着西装旗袍,这些都是昆曲难以模仿的,但昆曲自有过人之处,“它的唱腔的那种柔绵,以及形而上方面的深度思考”,这些都是帮助昆剧创理解其根源与本质的路径。
在张军眼中,现代昆剧《瞿秋白》便是一部“特别昆曲”的戏。剧中没有大起大伏的故事情节,只以“昼”“夜”作为虚实两条线架构全剧,深刻剖析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昆曲就擅长干这个事,”张军拈出老戏《亭会》作比,“亭子里相会有啥好演的?45分钟。你来我往,给你一点点把小情绪放大。”
生长于台湾的当代传奇剧场,更看重戏剧的无界限与时代性。吴兴国想起老先生常说的“学时一大片,用时一条线”,实为不刊之论。放开眼界学习各种东西后,在新的创作里,无论是角色本身,还是舞美服饰,若形成统摄的美学风格,那样的作品便不再浮于杂乱的拼贴。
剧校毕业后,吴兴国被保送进入戏曲学家俞大纲所在的文化大学深造,由此接触西方戏剧。同时,他加入林怀民刚刚创办不久的现代舞团体“云门舞集”,接受了一种全新的表演训练方式。舞者的课程,除了舞蹈之外,还包括文学、音乐、美术、书法等,亦会听演讲、看电影、观赏民间草台班子演出,彼此讨论交流。这对吴兴国解放思想观念非常重要。
创办自己的剧团后,国际交流频繁,他愈发感到传统与经典的当代化是多么重要。1990年,《欲望城国》被邀请到英国演出,吴兴国受邀去看话剧《哈姆雷特》,那版的主演是电影《布拉格的春天》男主演,剧本没有太大改变,还是按照原本的次序去完整讲述故事。剧场坐满观众,但演至三分之一,吴兴国回头一看,三分之一的人睡着了。“现在的观众,很少人愿意再去看一个原封不动的、几个世纪前的莎士比亚的戏剧。”
吴兴国在台湾演出时,许多观众老早就知道他要改编哪部作品,但没有进剧场之前,无法预期会是怎样的一台戏。比如歌剧《凯撒》,如果将它按照《欲望城国》的方式来创作,就可以把古希腊语境挪到同时代的古中国,用京剧文武场、线性叙事完成。他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无论何种形式的创作,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绝非之前哪个时代的复制品。
传统在身
在排演新编昆剧《春江花月夜》时,张军起初对导演说,要把剧中一个对现代观众来说很难懂的典故删掉——编剧罗周笔下,辛夷闻张生之死,年年至明月桥做“阮步兵哭兵家女”之举,感叹青春丧亡,生之易死,死之难生。
随着表演的推进,张军意识到,全戏彻底的升华,恰恰在于这个典故所反映的情志的深度。在许多讲座中,他都会拿这个部分出来分享,“有的时候昆曲最难懂的东西,恰恰是它生命之所在”。但这不意味着演员拿昆曲来简单唱一遍,观众就有感觉,艺术家需要多方面挖掘其背后的精华,也许是一句唱词的诠释,或是整个音乐氛围的营造,抑或是对昆曲背后人文历史的严格的铺陈。

2023年12月8日,张军(左)在江苏昆山梁辰鱼昆曲剧场主演昆曲《春江花月夜》。视觉中国
当了校长以后,张军一直向老师学生们强调,虽然在大家眼中自己是一个比较先锋的昆曲演员,但他认为,“戏曲学校这六年首先是削尖脑袋认清思想,你得把传统学好,你在台上,你的唱腔咬字,你的所有的传统能量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去走所谓的发展的路?”
许多院团在继承传统戏,有时不惜一招一式地复刻前辈,张军觉得太有必要了,演员你来我往之间细腻的勾连,唱腔的抑扬顿挫,都是老祖宗非常重要的财富。
吴兴国同样致力于京剧传承和教育。2010年起,他设立“传奇学堂”,邀请两岸京剧名家,在暑期对台湾年轻人才进行集训。连续十多年做下来,有40多个学员成长为京剧新生代演员。“所以才会有现在(《凯撒》)台上看到的这6个人,是那40个里面的6个。”林秀伟很欣慰,这群台湾京剧传人,有12个留在了当代传奇剧场,其他人也在各个剧团里发光发热。
看完当代传奇剧场的作品,一些熟悉戏曲的观众评价,舞台上有很传统的部分在。这是吴兴国与他的剧团不易被察觉的一面。“我到现在为止,几乎每个戏都不太一样,但是从没有离开手眼身步法,唱念做打,甚至于生旦净末丑,”吴兴国的语气认真,话音未落又大笑起来,“只是你没感觉。”
他一直坚持戏校时期培养起来的每天吊嗓子的习惯,唱的皆是老戏。每一年,他都要保证剧团的12个年轻演员有传承的剧目。
“不管是哪个地方剧种,统统都是唱念做打,我们的传统理念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的。”吴兴国十分珍视戏曲蕴藏的综合性,尤其作为演员,这些便是他最大的养分与能量。
成立五十多年的法国太阳剧社,多次邀请吴兴国去教学。艺术总监亚莉安·莫努虚金看了他的表演,发出赞叹:中国戏曲演员太幸福了,有一套这么完整的传统,从肢体、声音到表演,而他们在创作时,需要从各个剧种中分别获取养分,比如从意大利喜剧中找到肢体表演的方式,从歌剧里获取声音的训练。
吴兴国慨叹,“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林秀伟也为京剧表演体系未能进入国际讨论感到惋惜,“(日本戏剧家)铃木忠志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京剧更有,但京剧没有人去书写”。
2023年,当代传奇剧场进驻新北板桥放送所,拥有了自己的剧场。接手后,林秀伟才发现,这个古迹文创园区的水电设施问题严重,募集的钱不够用,吴兴国拿自己房子去贷了款。他向林秀伟举例,尚小云当初把六合院都卖掉了。林秀伟也听闻过一些台湾戏曲界人士的事迹,明华园歌仔戏团的孩子就曾告诉她,为了养戏班,爷爷二十几栋房子都卖光了。
剧团如今背负着5000万新台币的债务,依旧需要像过往兵分三路——从政府、企业、票房获取资金。林吴二人问过年轻团员,愿不愿意一起投入,一起承担责任。他们都说愿意。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刘悠翔
结论不断地试验,最终取得了卓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