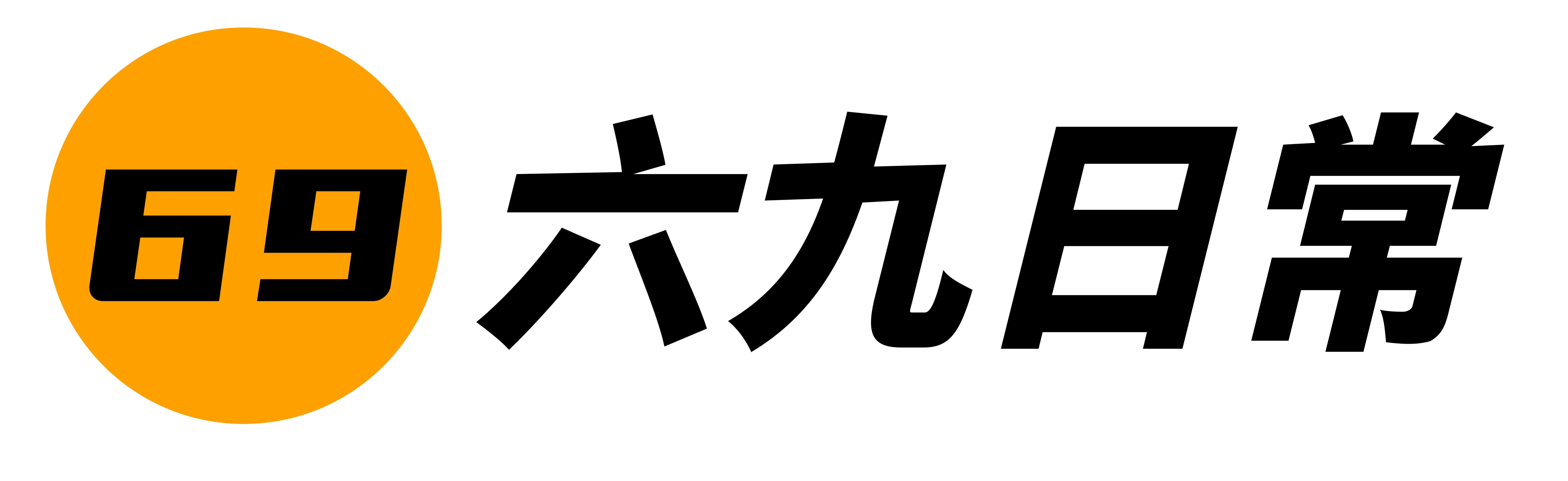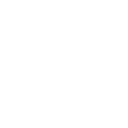1916年6月6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不止一个版本,最流行的说法,无疑是那句“他害了我”。与此相应,待袁世凯死讯传出,时人纷纷感慨他为小人所蛊惑,倒行逆施,忧惧而死。譬如曹汝霖称“一世英主,惑于佥壬,一念之差,贻恨千古,可悲也夫”——“佥壬”即小人;王锡彤说“一班宵小益得以种种媚术蛊之,而洪宪之祸作矣”;张謇哀叹道:
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那么,袁世凯口中的“他”与时人眼里的“佥壬”“宵小”“群小”等,到底是谁?
张瑞玑《吊袁项城》诗云“有子不才误刘表,失计无端听蒯通”。稍通史事,可知前半句指袁长子袁克定,后半句指其幕僚杨度。
彼时若论袁世凯称帝谁最热心,谁最卖力,将来谁收益最大,答案都是袁克定。帝制运动的关键环节,皆可见他的忙碌身影,如筹安会之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之组建等。最出格的行径,则属篡改《顺天时报》,伪造舆论,误导其父。是以在袁世凯病情最严重的时刻,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曾冲袁克定抱怨道:“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曾抚棺痛哭;王锡彤前去吊唁,安慰袁家诸子,袁克定“自称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致贻祸老父”。不过舐犊情深,袁世凯并未降罪于长子。据袁七子袁克齐回忆: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日),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这么说,则把袁克定视作受害者,那句“他害了我”与其无关。
相比悔恨交加的袁克定,杨度态度相当强硬。作为《君宪救国论》的执笔者与筹安会的发起人,他认为袁世凯辜负了他所守护的君主立宪制。试看其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边厢,杨度否认自己害了袁世凯;那边厢,袁世凯的遗言,在一些场合直接变成了“杨度误我”。1916年7月14日,官方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列出八名要犯,杨度排名第一。
关于杨度,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军师、帝王师、心腹幕僚等。事实上,杨度进入袁世凯幕府,为之出谋划策,迟至武昌起义之后,比王锡彤还要晚。民国初年,他不受重用,郁郁寡欢,欲对袁世凯施加影响,有时还得借重他的师兄、时任总统府内史的夏寿田。其时袁世凯手下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之说,这里面,徐世昌、赵秉钧、杨士琦、梁士诒、阮忠枢、张一麐等,与袁世凯的亲信度,以及袁世凯对他们的倚重,都在杨度之上。
进而言之,即便杨度是袁世凯最亲近的幕僚,便可令主公言听计从吗?须知袁世凯既有海纳百川、礼贤下士的一面,同时极具主见,极其自信以致自负,从不轻易受人左右。据黄远生观察:
……在其(袁世凯)平日能容颐指气使之人,而不能容师友及平等之人,故能进规随之谈,而不能容忠谅之士。故夫巧谋杂计,其所喜也;直言新策,其所怫也。
说白了,袁世凯只能容纳支持他的人,不能容纳反对他的人;只能听取赞美他的话,不能听取批评他的话。拿复辟帝制来说。大幕拉开之时,赵秉钧已经去世,徐世昌模棱两可,严修、张一麐、王锡彤等均表示反对。论分量,这些人的意见显然都重于杨度,却因不合袁世凯心思,统统被抛诸脑后。反过来讲,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采纳了杨度的意见,而是因为他本来便作如是想。故而丁中江说:
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袁世凯的自负,另一面则表现为担当。1916年3月22日,他召张一麐进宫——张一麐因反对复辟帝制,被袁世凯有意闲置——主动道歉,“予昏聩,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不可”。令即《撤消承认帝位案停止筹备事宜令》,一般称《撤销帝制令》,原由接任张一麐政事堂机要局长一职的王式通起草,袁世凯不大满意,请张一麐重拟。张一麐建议直接撤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随之宽解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世凯则答:
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
撤销帝制之后,袁世凯与张一麐重归于好,常常扺掌而谈。他反思道:
……(张一麐、严修)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他害了我”,与其生前三番五次强调“不能咎人”“不必怨人”的情节严重不符。相形之下,另一版本也许更加可信。袁世凯临终之时,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等守在病榻边上,徐世昌问:“总统有什么交代?”袁世凯竭力吐出两个字:“约法。”
张瑞玑诗云:
死不灰心真健者,生能悔过即英雄。(张瑞玑吊袁世凯诗共两首,对袁氏整体评价不高,唯此二句如异军突起)
羽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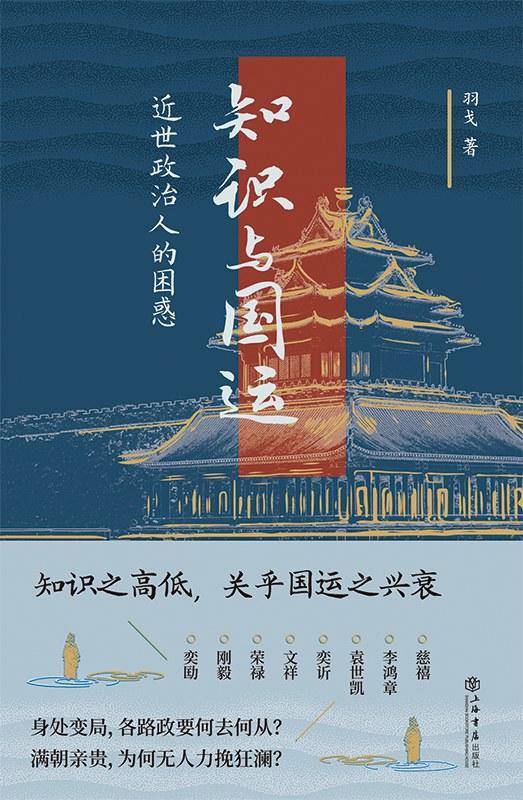
《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