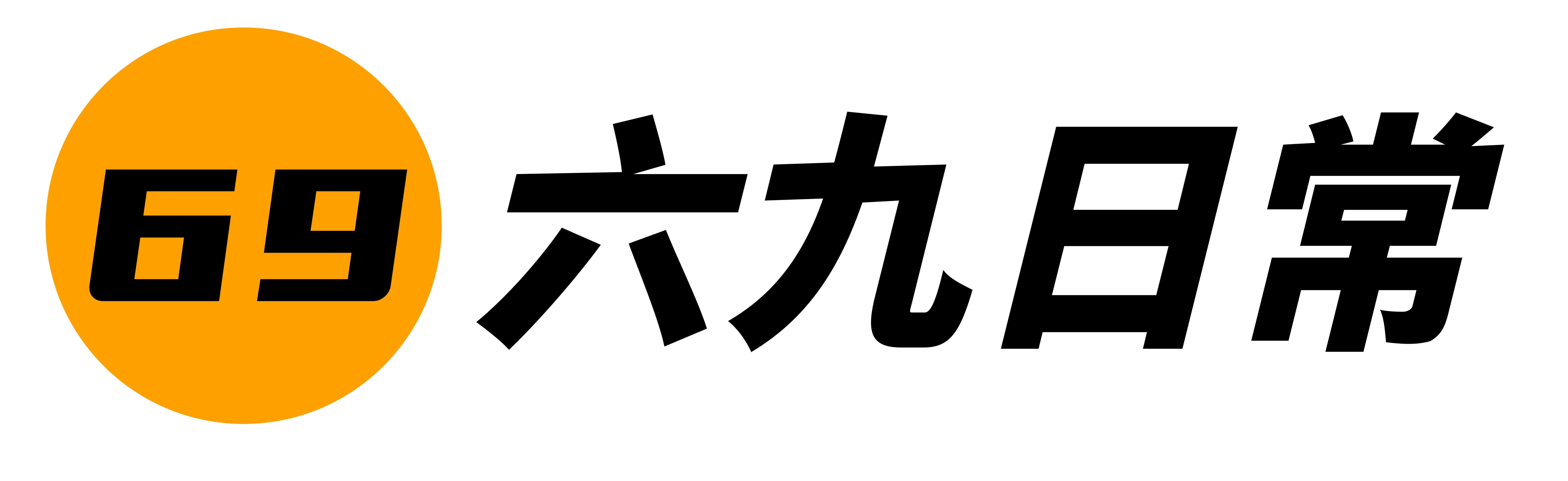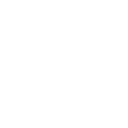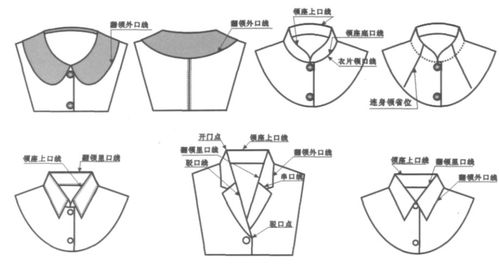常言道“知识改变命运”。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为莘莘学子“逆天改命”提供机遇,也为皇权社会下的官僚体系选拔必要的人才。不过,科举竞争异常激烈,不亚于当下父母“鸡娃”,培养孩子考上一流大学。可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仿佛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考取功名后,读书人的生活便一帆风顺吗,抑或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节点?历史学者王瑞来的《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上,给予我们颇多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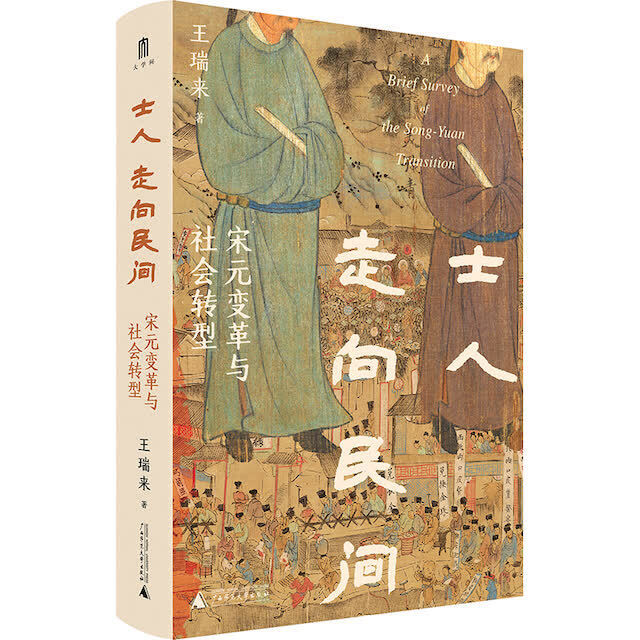
《士人走向民间》
王瑞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读书人的“两道门”
从北宋到南宋,科考人数增加,录取名额却没有激增,于是南宋科举变得更加“内卷”。比如吉州(今江西吉安),北宋末年应试人数4000人,录取名额45人,而南宋录取人数增长至68人,可应试人数已经超过万人;更残酷如福州,北宋末至南宋初,应试人数3400人,录取名额68人,到孝宗开禧年间,应试人数暴增至18000人,而录取名额竟然降至54人。可见,哪怕学习水平不变,生在不同时代,结局恐怕也将大不相同。
古代士人读书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做官,可即便进士出身,也要经历漫长的爬升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说,科举难,仕途更难。中考进士一般会被授予低级别的幕州县官,当时习惯称之为“选人”,中考者要经历选人、京官、升朝等步骤,直到散执政,否则整个仕途都可能在各个地方任上蹉跎。
选人之内的升迁,非常困难,时人唤作“选海”。以选人七阶内迪功郎为例,有进士出身者经历三考,无进士出身者要求四考,也就是担任差遣三年或四年,所谓“考”就是对官员一任的考核与迁调;如果没有举主推荐,还要经历五考。可以看出,进士出身只是做官的“敲门砖”,只是一定程度有所加成,并非起决定性作用。
要脱离“选海”成为京官,最重要的是上司推荐。《朝野类要》记载:
承直郎以下选人,在任须俟得本路帅抚、监司、郡守举主保奏堪与改官状五纸,即趍(同“趋”)赴春班改官……选人得初举状,谓之破白。末后一纸凑足,谓之合尖,如造塔上顶之意。
也就是说,五封推荐信,才是仕途更进一步的关键。然而,不难想象,“推荐”制度中人的因素干系甚大,无门路者想要拿到足够分量或数量的推荐信,可谓难上加难。南宋洪咨夔就曾评价为“矧堕七选之坑,欲结五剡之塔。”
由此,王瑞来深刻地总结道:宋朝的政治家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充满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门……穿过这第二道门,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读的真正目的。然而这第二道门却是不易穿过。穿过第一道科举之门,尽管千里拔一竞争激烈,但毕竟主要凭自己的努力,顶多是加上家族的财力支持。如果成绩不成,神仙也帮不上忙。然而,穿过第二道入官之门时,却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运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选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绩这样的“硬作为”,以及广结人脉、钻营于权门这样的“软作为”。对于这第二道入官之门,多数选人是“小扣柴扉久不开”,甚至对有些选人而言,门是永远关闭着的。

【宋】李唐《雪窗读书图》
杨万里也难免俗
南宋四大家之一、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诗歌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言。然而,他的仕途绝非一帆风顺。
杨万里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举,获得选人身份,授官赣州司户参军,又因为员多阙少,杨万里在家待阙两年后,才正式入职。直到37岁,杨万里还在零陵县丞的职位上,看上去前途晦暗。
他命运的转机来自于结识张浚、张栻父子,当时朝廷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贬谪于永州,杨万里有机会师事张浚。此后,孝宗即位,主战派张浚出任宰相,杨万里随即改秩左宣教郎,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得以脱出选海。

杨万里像
杨万里无疑是幸运的,可他的生活也是贫瘠的。他在39岁丁父忧居家时,以《悯旱》描述了生活的贫困:“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杨万里后来官至吏部员外郎,他一生最荣耀之时,应当是孝宗亲自将其升为东宫侍读,太子赵惇,也就是后来的光宗,亲题“诚斋”二字赠给他。
作为一名诗人,杨万里生性放旷,注重声名。他自言:“士大夫穷达,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即便如此,杨万里的文集中,却充满了为亲友子孙求取推荐的信笺,约占比三分之一。这也侧面说明,在既定规则下,一代文豪也不得不遵循人情世故。最终,在杨万里的不懈斡旋之下,长子杨长孺终于在几年内连续升迁,脱离选海,踏上光明的仕途。
俗谚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被提点并改变命运的杨万里,当然深知游走于体制的不易,如果不能跳脱规则,任何人都只是这部官僚机器的“齿轮”。
读书人如何灵活就业
南宋科举竞争激烈,而到元代更是停废科举。由宋至元,很多举子无法在仕途精进,于是自谋生路。那么,这些读书人可以做什么呢?不妨从他们掌握的技能一探究竟。
《儒林外史》里有个马二先生,热衷科考,他并非成体系地学习,而是利用范文、例文来应付考试,属于极为功利的学习。然而,这种情况在宋代业已出现。辛弃疾年轻时从金国境内的山东,回归南宋域内。辛弃疾对当时的科举不以为然,认为花上三百铜钱购置时文教科书便可考中。随后,他果真中举,孝宗还不无打趣地说辛弃疾的官爵是三百个铜钱买来的。还有一例,陕西人姚岳流落四川,得到一册举业时文,才发现自己之前学的东西很“落后”,于是加倍吸收,最终也得以中举。
以上事例并非否定科举的价值,只要是考试,必定有规则,也必然可以提升效率。程式化的事物不可避免,人们无非是在规则中占据先机。
对于时文、公文的熟稔,促成了元代“以官为吏”的现象。唐、宋两代中,举子可做县里的一把手或二把手,而真正执行政策的群体是胥吏,官、吏虽然并称,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官可升迁,吏只是“打工”,所谓“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衙役”,二者属于两个阶层。
元代以蒙古人、色目人作为领导阶层,汉人、南人只能负责基础治理,鲜有上升阶梯。但废除科举后,行政治理依然需要文士,于是便出现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1267)的一段评价: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具备文化知识的士人,转职为胥吏,可以说只有心理障碍要突破,本身的能力已经具备,相当于以大材作小用。然而,世道如此,读书人也别无选择。除胥吏外,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谋生选择。
元代还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设有“儒户”,所谓“户”就是职业和身份相融合的户籍制度。将士人与贩夫走卒并列齐名,当然在“士农工商”的观念中充满抵牾,可是,客观上儒户免除赋税,又让他们充满优越感。
所以,“士人作为世袭的文化贵族,不凭借祖上的血缘门第,在元代终于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比较社会的其他阶层,拥有不纳税、免除大部分差役特权的儒户,成为社会中以文化为标志的精神贵族群体”。吊诡的是,正是废除科举,将士人身份变为户口标识的元代,加强了士绅阶层的形成,将这一宋元改革延续至明清,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过往观点容易夸大废除科举的影响,其实,元代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废科举、变儒户、做胥吏,无疑说明那些看似坚固无比的“身份”,很可能变动不居。
黄公望另辟蹊径
《富春山居图》的、大画家黄公望,生活于元初,一生坎坷颇多,从事职业甚众。黄公望自幼读书,“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在继父去世后,黄公望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胥吏大军。

黄公望像
在《录鬼簿》一书中,描述黄公望“浙西宪吏性廉直,经理钱粮获罪归”。黄公望因工作而获罪,推测他得罪了地方权贵或顶头上司,导致为吏生涯草草收场。后来他加入全真教,《姑苏志》记载:“黄冠野服,往来三吴,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三教中人,多执弟子礼。”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其实是黄公望为教友无用师而作。
此外,黄公望“以卜术闲居”,说明打卦算命也是他的谋生手段之一。《大清一统志》记载说松江“其地有精《九章算术》者,盖得其传也”。打卦算命,需要精通算学,后世还有以他为名号的传人。
由此看来,黄公望的职业履历非常丰富,属于典型的灵活就业,自谋生路。相较于胥吏、宗教人士、卦师,作画亦可视作他从事的众多行当之一。
据黄公望两次从吏时间看,第一次在20至30岁之间,第二次则接近50岁。30至40岁的年龄段是黄公望履历中的空白。或许在“经理钱粮获罪归”之后,他便开始学画,自己因“廉直”而仕途受挫,是时开始自号大痴,亦属合情合理。
黄公望位列“元四家”之首,在历史画坛地位甚高,然而,黄公望的绘画,多少有半路出家的意味,至少从他的生命轨迹看,并非自幼就有追逐艺术的理想。
难得的是,黄公望晚年不断创新,作画不辍,让绘画成为自己一生中真正的追求。恰如王瑞来所言:“滴水映日,写意传神,透过黄公望个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还是一个时代的云涌风动,是裹挟着无数浪花的大河奔流。”在任何时代,人的命运由自己抉择,但也绝对离不开所处时代给予他的影响。拿起、放下、权衡、变更……这些或许正是动荡时代中不可避免的常态。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