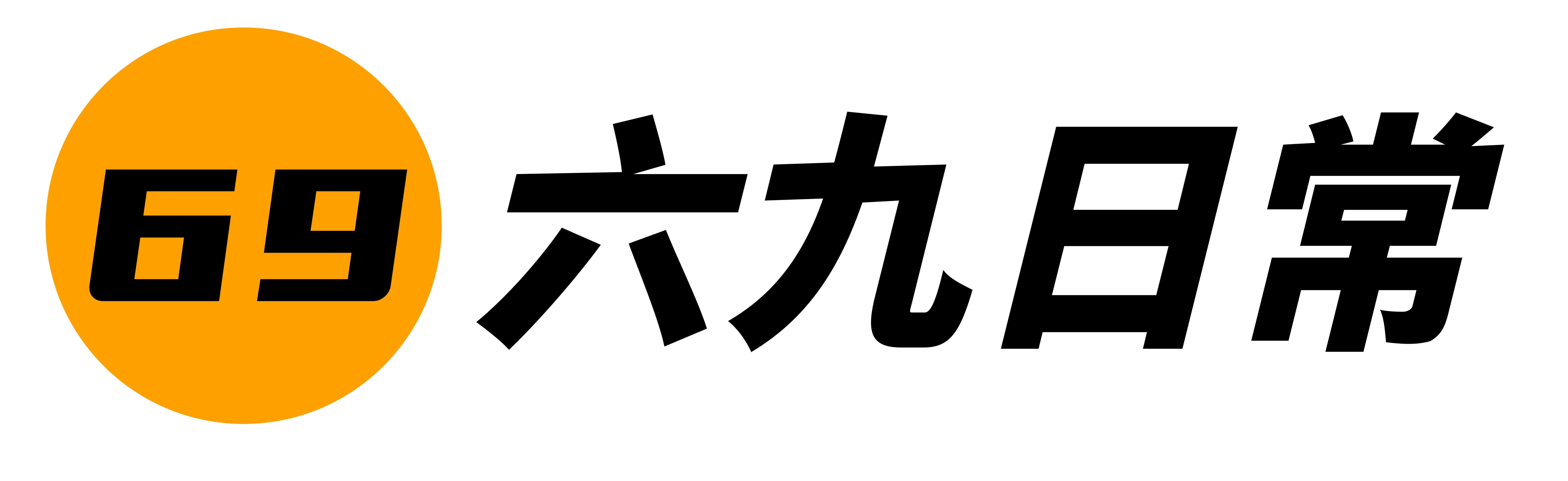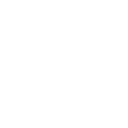从高处看我们,就像风中的草。
一
酒吧灯光昏暗,29岁的罗永浩挤在诗人和作家中间,忘情喊着“安可”,要求返场。
人群从舞台边一路挤到门口,简陋木门外,是灰尘蒙面的三里屯南街,夜风放浪奔跑。
酒吧名叫“河”,面积不过15平,却被称为“中国当代民谣的母亲河”。
小河、周云蓬、万晓利、左小诅咒在此登台演唱,众多乐迷和歌手,将其视为理想国和乌托邦。
没有玩骰子的观众,没有一掷千金点歌的大哥,乐手们抱着吉他,即兴弹唱,台下歌迷敲着酒瓶烟灰缸相和,有时兴起,还会冲上台跟着高歌。
无论台上的歌手还是台下的酒客,共同特点都是穷。
河酒吧不收门票,不强制消费,很多人进门前,会从隔壁小卖店买几罐啤酒揣进兜。
午夜气氛高点时,没什么钱的酒吧老板小索,会拍桌子大喊“给每个人上一扎啤酒,记我帐上”。
歌手小河怀念那些酣醉的夜晚,掌声,碰杯声,欢呼声起伏如海浪,他抱着吉他,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喝多了就去街上和人拥抱,还邀请趴活的的哥“一起跳个舞吧!”
那年,他和万晓利组成乐队“美好药店”,每周三在河酒吧驻唱。
两人从天通苑坐三小时公交车赶来,半夜打车返回,赚的钱还不够路费,但依旧满心欢喜。
歌手张玮玮说,“河”有引力。2001年北京大雪,全城交通瘫痪,他和朋友堵在东坝去三里屯路上。
他心血来潮,下车和朋友沿着马路滑雪向前,两人一路欢声,就这样滑到河酒吧。
八十年代的理想,九十年代的躁动,换了载体延续,那些年的人、事与歌,都带着无畏。张玮玮说:
“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一切都太美了。”
空山乐队主唱蒋明,曾慕名前往河酒吧,看着台上发呆:一群来自民间的歌手,在一间漏风房子里唱着自己的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2010年,在豆瓣发歌的宋冬野,结识了马頔和尧十三,三人拉了个QQ群和歌迷聊天。宋冬野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河酒吧”。
马頔和尧十三挤进宋冬野五环边的破房子,前往各个酒吧驻唱,唱够了就去喝酒,兴起便光着脚在东三环下狂奔,仿佛跑回旧时光。
同年,“民谣在路上”巡演进行,朴树复出、沈庆登台、老狼奔走,民谣歌手们搭绿皮火车,边走边唱,一路向南。
唱完最南一站广州后,有乐队坐飞机返京,因华北大雾,飞机备降武汉机场。
滞留机场时,候机厅里人群焦虑抱怨,场面混乱。
老狼乐队的乐手小彭忽然吹起口琴,山人乐队拿出了鼓,沈庆抱起吉他,歌声开始流淌:
“幸福它在哪里?幸福它太贵啦,跟我没关系……”
人们慢慢围拢,脸上多了笑容,有人跟着节奏跳舞,更多人拍手相和。那更像民谣本来面目:在路上,在人群中。
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没有人愿意停下。
二
1990年,青海运输公司的张佺,结识了兰州棉服厂的小索,两人因音乐一见如故,结伴闯荡。
5年后,他们在西湖边成立野孩子乐队,回望西北,写下那首《黄河谣》。
隔年,野孩子乐队进京,住进地下室,排练只能在三元桥下草坪,头顶常有汽车飞驰而过,轰鸣声淹没歌声。
周云蓬同年来京,每天卷张大饼,背吉他街头卖唱,运气好晚上能喝上啤酒。
万晓利则在颐和园边租了间小房,录歌无人相识,他在歌中写道“夕阳染红了大地,你天天在这干什么呢?”
北漂数年后,朋友建议小索:三里屯有小画廊在转让,盘下来做酒吧,乐队能排练,演出还能赚点钱。
2001年,小索和朋友四处借钱,开起“河”酒吧,开业那天,野孩子唱了那首《黄河谣》: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河酒吧的畅快时光,只存在不到三年。
非典后,本就亏损的河酒吧摇摇欲坠,夏天停业转让。张佺和张玮玮站在酒吧前,默然看着“河”字被拆下。
隔年十月,小索因胃癌去世。张佺一夜白头,背着冬不拉流浪远方。
张玮玮坐绿皮火车去了新疆,火车一路过伊犁,过喀什,他也不知自己在寻找什么:
“小索的去世,就像是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美的梦,突然一下被扯得粉碎,让人清醒无比。”
新疆归来后,他发现连三里屯都易主了,卖给了潘石屹。
离开河酒吧,万晓利在天通苑的住所继续录歌。2006年,经老狼推荐,他发行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那年高三的马頔,逃课来听首发会现场,听得泪流满面。
宋冬野则买下这张专辑,坐在中关村广场上,听专辑里第一首歌《陀螺》。他边听边哭,从下午四点单曲循环到晚上十一点半。
万晓利一夜成名,北京地铁1号线甬道内,贴着他的巨幅照片,报纸上称他为“后民谣时代的鲍勃·迪伦之子”。
然而,万晓利不喜欢。他走在路上局促不已,拒绝所有邀约,最后如朴树一样,逃离喧嚣。
2010年那场“民谣在路上”,更像短暂昙花。更多时刻,民谣要接受商业的浸染,接受同化或剥离。
《新周刊》主笔胡赳赳撰文,民谣歌手是“末路音乐人”。
宋冬野签约了摩登天空,但也没什么歌迷。直到2013年,《快乐男声》翻唱《董小姐》,酒醒的宋冬野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这首歌。
此后,马頔的《南山南》也在综艺上被翻唱,一夜间“多了几万条艾特”。韩寒电影用了万晓利的《女儿情》,而罗永浩把张玮玮的《米店》预设成锤子手机铃声。
民谣走出地下,流量滚滚而来,随之出现的是大量单曲播放破万的“转基因民谣”。
那些民谣曲调雷同,歌词矫情,总离不开小镇和姑娘,创被乐评人称为“一群僵尸文青”。
宋冬野开始讨厌《董小姐》,称其“最恶俗”。
马頔则后悔写《南山南》,“为什么我不写这种歌了?因为爷们要脸。”
赵雷火了后,不论参加什么活动,主办方只有一个要求,“唱首《成都》就行”。最后他在台上爆了粗口“特别想对主办方说一声FUCK!”。
2020年,梁文道给民谣小史《沙沙生长》写推荐语,说书名是生长,听见的却是落叶成堆的沙沙声:
“希望这一切都是春天的故事,但事后回想,只怕那是深秋灿烂。”
三
今年3月,赵雷歌里的小酒馆关店,而比小酒馆消失更久的是民谣。
民谣消失在春风里。那些野生的歌声,始于生活,寄于理想,又逝于商业和规则的合谋。
它骨子里其实是锋利的,是底层倾诉的心声,是人间的底色。
2005年,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出版新专辑,赞誉如潮,他却极不自在:
我唱歌无所求,我所歌颂的山川和人们,早已给我所需的……云海、山脉和清流,和波涛。
八十年代,他写歌为被拐雏妓发声,写歌拷问矿难爆炸原因。他说,民谣的初衷,就是为受苦人唱歌。
已退隐的民谣歌手杨一,九十年代背红棉牌吉他远游中国,一度被关入收容所。
每天,他与三无人员、流浪汉、乞丐一起目送夕阳。那些个黄昏,他为这几百人唱歌。
离开后,他浪迹全国,在街头唱歌,代表作叫《烤白薯》,唱的是底层的小贩:
“他又上街卖烤白薯,东张西望躲着工商。北风吹呀吹不走这里的病,看见他总是孤孤单。”
小河的《老刘》歌词取自《北京晚报》的社会新闻,周云蓬的《失业者》唱的是服务员、仓管员和推销员。
万晓利在河酒吧现场录的首张专辑,唱着自己坐公交奔波的岁月,还有下岗职工的故事。
《董小姐》和《成都》,唱着被时代无限放大的孤独,和不足为外人道的失望。
那些犀利是民谣的灵魂。
2020年,野孩子参加音乐综艺,拒绝改编流行的“网络神曲”,最后选择退赛。
他们留下句话:真正的民谣不是流行,是流传。
过往三十年,歌声如江河,摇滚如黄河瀑布,湍急咆哮;民谣则如长江入海,开阔平静。民谣犀利度甚至超过摇滚,只是如今,水流已沉入大地。
多年以后,张佺追忆河酒吧时说,河水携带着种子默默流过干渴的河床,从不向高处。
而小河则说,民谣的生命力在于现实,不是最漂亮的浪花,而是底下不绝的河流。
他的寻谣计划已做了五年,就是为收集那些隐匿民间,口口相传的歌谣。那是真正河流里的歌。
2012年,张玮玮专辑《白银饭店》中,描绘了一段戈壁滩上的故事。
白银饭店每晚都要举办舞会,人们唱歌跳舞,边喝边哭,不停拥抱,每个人都说自己第二天就要走了。第二天,舞会再次上演。
这好像张佺记忆中河酒吧那些个夜晚:后半夜,喝得都差不多了,台上台下都在唱着,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好像认识,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