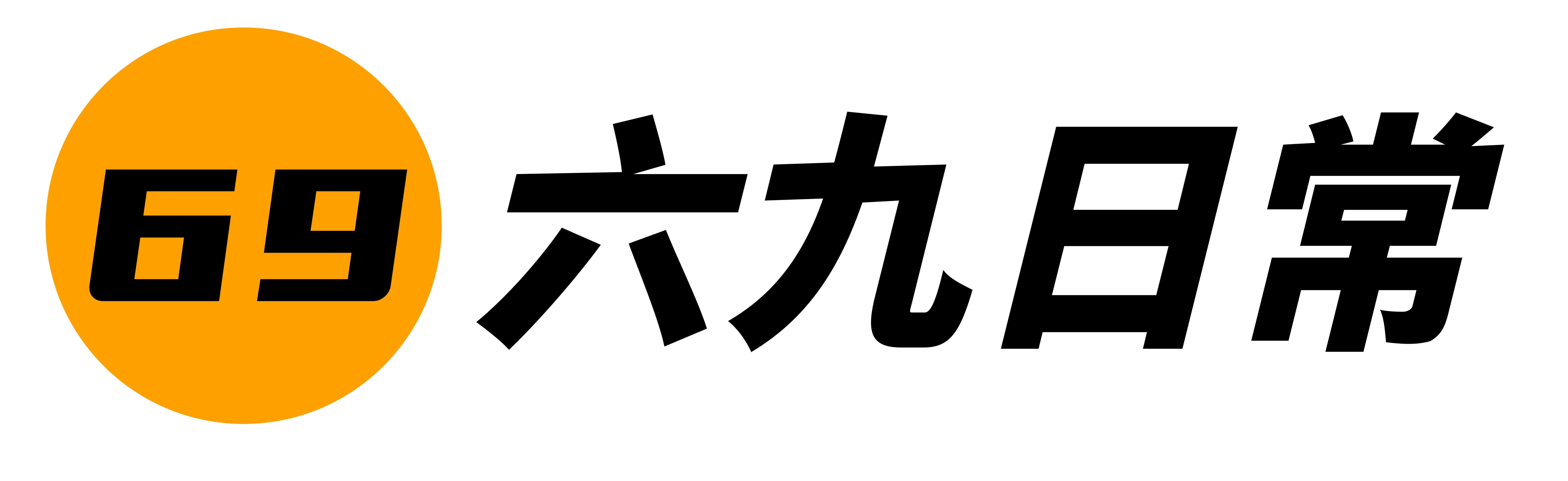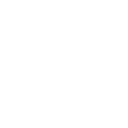1860年9月22日清晨,北京城外兵荒马乱,圆明园内仓皇逃出一支队伍,其中有位身份特殊的人,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苦命天子”的咸丰帝。
就在几天前,英法联军攻破天津大沽炮台,沿北运河一路杀向北京,又于京郊的八里桥击溃前来阻击的清军。前方再无遮拦,京城岌岌可危。咸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狩”承德,他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位出逃京城的皇帝。
因缘际会,2023年秋冬时节,我有机会先后走访了承德、大沽口、野狐岭。回来整理资料时突发奇想,在地图上把三个地方用直线连接起来,一座城市、两处要塞,形成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而北京恰好处在底边的中点上。当我继续梳理历史脉络,发现这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在时空的旷野中,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武烈河在承德穿城而过。 摄影 张佳
天子北狩
我在仲秋时节乘动车从北京前往承德,一个小时的车程,出发时尚有夏季余热,下车后却已秋风萧瑟,凉意颇浓,塞外气息扑面而来。出租车司机如数家珍地介绍承德的风土人情,言语间颇多自豪,提及木兰围场,他却意兴阑珊,“坝上树叶都落了,天冷,路也不好,这个时候没啥好看的”。
承德以避暑山庄闻名,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离不开燕山。这座横亘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山脉,在承德绕出一个巨大的“U”形,就像一座巨型大圈椅,背靠莽莽苍苍的群山,两侧山体犹如扶手,将城市围在中间,武烈河在正前方穿城而过,避暑山庄就坐落在“大圈椅”的靠背处,坐北朝南,向阳而立。
两侧“扶手”上还分布着外八庙,共同构成承德避暑山庄建筑群。咸丰的祖上之所以建造这么一个去处,除了名义上的“避暑”,更意在怀柔远人,没想到成为后代的避难所。
咸丰去世时才31岁,逃往承德是在他生命倒数第二个年头,这里也成了他人生最后一站。那么,在山庄的日子里,这位年轻的皇帝会是怎样一种心境?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记录着祖先们的丰功伟业,可到了自己这里竟至一塌糊涂。他虽资质平平,但早年也曾意气风发,苦修儒家经典,恪守“祖宗成法”,为平定叛乱,不惜掏空皇家的小金库(内帑),希望通过励精图治实现中兴,奈何王朝的颓势已不可避免,终其一朝,内忧外患不断,江南的刀兵、海上的硝烟、洋人的蛮横、臣子们的阳奉阴违……他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终于心灰意冷,躲在这片山水之间纵情声色,直至去世。

在普陀宗乘之庙御座楼眺望承德。 摄影 张佳
换个视角来看,在历史图谱中,承德还有另一层意义。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凡入主中原后都热衷于修长城,以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劫掠。但满清是个例外,他们以弓马骑射起家,早期就屡屡撞开长城进入关内,并最终夺取天下,因此当然知道,这道墙根本挡不住来自北方的威胁,不过是图个心理安慰罢了。
我曾去过金山岭长城,它因由戚继光主持修建而著名,号称明长城中“构筑最复杂、楼台最密集”的一段。完备的城防加上骁勇善战的戚家军,让蒙古骑兵不敢再轻易犯边,“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对戚将军来说,修长城实属无奈之举,他和他的戚家军以善于进攻著称,这在扫灭倭寇的战斗中得到证实。但北方的局势或者说朝廷的实力无法支持他主动出击,因此只能采取折衷办法。他去世不久,戚家军奉调出关,在与满洲旷日持久的争战中消耗殆尽,再坚固的长城也无人防守了。
“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康熙总结前人得失,选择修建另一种形式的“长城”。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北巡期间决定在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旗设皇家狩猎牧场,即木兰围场,在承德市正北方约180公里处。
这是一个绝佳的练兵场,北缘是阴山余脉,南缘是燕山余脉,中间分布着草原和丘陵,正适合游牧骑兵纵横驰骋,康、乾两朝,皇帝曾多次到此秋狝。但所谓秋狝,除了狩猎,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沙场点兵,参加者除了皇室贵胄、王公大臣,主要是驻防京畿的八旗劲旅,有时全国各地的驻军也会派代表到场观摩,人数达万人以上。这么庞大的队伍,吃喝拉撒都是问题,于是在沿途修建行宫,这便有了承德避暑山庄。
除了练兵,秋狝还有震慑北方草原诸部落的意图,毕竟,前明的教训就摆在眼前——先是被蒙古袭扰,边患不断,后又长期苦于满洲,最终被拖垮。康熙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据史料记载,他每年秋狝,都要在行宫接见蒙古王公贵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首领,并带他们随行观看规模庞大的“狩猎”。恩威并施之下,北方草原大体保持了稳定。
而如果将视线拉长,康熙帝决定设木兰围场也许跟另一个地方有关,那就是野狐岭。
风雪野狐岭
野狐岭在承德西南方向三百多公里处,隶属张家口。我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抵达,夜宿市区,翌日清晨雪霁天晴,乘车去往野狐岭。
途中经过明万全右卫城遗址,它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上的重要支点,被称为“京西第一卫”,瓦剌寇边、土木堡之变,就发生在这一带,连皇帝朱祁镇都被人捉了去,似乎再次证明长城的作用有限。

明万全右卫城遗址 摄影 张佳
沿燕山山脉靠近华北平原一侧,分布着众多“口”:喜峰口、古北口、杀虎口……张家口是其中之一。所谓“口”,其实是连通游牧区与农耕区、位置险要的关隘,长城恰好将这些关隘串起来,人们用“口里”“口外”区分长城内外。从万全右卫城再往前,就到了“口外”,进入蒙古高原南缘。风势陡增,硬如刀锋,裹挟着积雪弥漫前路,竟然有西北“白毛风”的架势。
跟木兰围场一样,野狐岭同样被当地人称作“坝上”。“坝上气温要比市区低四五度……他们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早上就开始喝酒了。”在出租车司机的描述中,四十多公里的距离,气候与风俗差异颇大,酒亦成为民风彪悍的重要标志。
野狐岭和木兰围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处于从草原向农耕过渡的地带。蒙古高原到这里后遇到燕山,几乎戛然而止,天苍地茫的草原变成错落耸立的山峰。从野狐岭向南,燕山与太行恰好错开一个缺口,再往前就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草原铁骑一旦越过这个缺口,可以俯冲而下,直取华北、中原、江南……
它与满族的渊源比康熙决定设木兰围场早470多年,那时的满族还被叫做女真。1211年8月,成吉思汗率领10万蒙古铁骑与40万金朝精锐部队在此激战,这是一场决定国运、最终影响世界历史走向之战。此战之后,蒙古铁骑冲出草原,一支向前攻灭金与南宋,另一支右转向西横扫中亚、欧洲,还带去了“黑死病”,也被欧洲人恐惧地称为“上帝之鞭”。今日中亚与东欧的地缘格局,仍有蒙古时期的影子。
史料对这场战役记载寥寥,但我们不难想象其惨烈程度,要知道,这是当时两大最强悍游牧民族(此时女真入关尚不足百年)之间的对决。蒙古一方自不必说,蒙古高原上的常年征伐淬炼出令人恐怖的战斗力,并且战将如云。金国则是由完颜承裕等少壮派将领率领的精锐之师,不过,他们的作战经验大都是在与南宋的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即便人数绝对占优,在面对来自北方的虎狼之师时仍信心不足——虽然他们的祖先也曾彪悍如斯。
蒙古人很快洞悉了金军的破绽,“马足轻动,不足畏也”,于是率先攻占了野狐岭北山口獾儿嘴,拉开战役序幕。双方从清晨激战至日暮,战局陷入胶着,这时决定整场战役胜负的关键人物登场了,蒙古悍将木华黎“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金军阵脚开始松动。
与此同时,另一支蒙古军队迂回至金军身后冲杀。前后夹击之下,金军瞬间崩溃,于是,原本应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变成单方面屠杀,在蒙古铁骑的追杀下,金军“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直到十年后的1221年,丘处机率弟子途经野狐岭时,仍看到皑皑白骨遍布山野。
对于蒙古的威胁,金人多年前就有所察觉,因此在西北边界筑界壕、蓄精兵,苦心经营,如今毁于一旦,既失地利,最精锐的部队也损失殆尽,几乎再难组织与蒙古的野战。因此有史学家评价:金之亡,决于是役。

一位放羊老人在野狐岭要塞前走过。 摄影 张佳
原本跟司机师傅说好去野狐岭古战场,但昨晚大雪阻断了前路,只能半途而废。向北登上一处高地,朔风瞬间刺透身体,大地风雪弥漫,千里不见人迹,只有一排排风力发电机兀自周而复始地转动。
我的思绪如这漫天风雪,想到女真以善骑射著称,一度是中原王朝的噩梦,在靖康之难中对北宋百般凌辱。只不过,曾经骁勇无比的女真骑兵在进入中原后快速腐化,不习弓矢,结果时不过百年,角色就发生了互换。野狐岭之战后,金的北部边疆再无宁日,中都(今北京)失守,无奈迁都南京(今开封),直至城破国灭,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金”之女真与后来“清”之女真本系一脉,关于这段历史,博学多识的康熙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平定三藩叛乱时,目睹八旗将士腐化堕落、不堪大用,与叛军对垒几乎不堪一击,会不会警惕地想到数百年前祖先们的表现?那么,决定设立木兰围场用以练兵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我这样想着,风雪越来越烈,几乎将人冻僵。我们决定折返去野狐岭要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特殊国际局势下,曾在这里修筑工事拱卫首都。时过境迁,要塞今天开放为景区。不过被工作人员告知冬季闭馆,只能打道回府。

野狐岭要塞一角 摄影 张佳
离开时朔风依旧,冰天雪地中,一位老人赶着牛羊,从“野狐岭要塞”标识牌前走过,又消失在山坡下。
来自海上的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熙的“长城”取得了部分成功,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清朝北部边疆的传统边患相对最弱。但世界已发生巨变,大航海时代打通了全球航路,就在统治者们沉浸于过往,并且选择闭关自守的时候,历史的触角已悄悄转到海上,前所未有的危机爆发了。大沽口就是众多爆发点之一。
大沽口被称为“入京咽喉,津门屏障”,海河穿过天津市区后由这里入海,它背后就是天津、北京和华北,战略位置不言而喻。当年,清军曾在海河沿岸修建“威、镇、海、门、高”五座炮台,以防备侵略者入侵,但最终都以失败和屈辱告终。第一次是在1860年,咸丰出逃前不久,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尽毁。李鸿章主政直隶后,对炮台进行整修和扩建,倚为屏障。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攻陷大沽炮台,杀向北京。
于是我们看到,在咸丰出逃北京四十年后,他的妻子(慈禧太后)带着他的侄子(光绪帝),再次出逃。清廷随后与侵略者签订城下之盟《辛丑条约》,被迫拆除大沽及通往北京沿线的相关炮台。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从此之后,京畿门户洞开,侵略者们可以随时从海上登陆,影响国家的权力中枢。一个王朝的脊梁彻底断了。这似乎也预示着,距离一个轮回的结束不远了。

大沽口遗址博物馆左侧,秦滨高速横跨海河。 摄影 张佳
在大沽“威”字炮台遗址上,现在建起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用以缅怀历史、铭记耻辱。我抵达时正值北风肃杀,天色阴沉,炮台遗址上,一位父亲正向孩子讲述那段历史,另一位年轻人脸色肃穆地站在垛口前,一动不动,形如雕塑。
在他面前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滩涂,正是清军曾与侵略者激战的战场,百年沧桑,海河在不远处依旧流过,不同大小的船只你来我往,百舸争流。炮台左侧也是一片滩涂,枯黄的芦苇在荒野中迎风凌乱,几只锈迹斑斑的大铁罐遗弃其中。硝烟早已散去,时光永久尘封,但那段历史不会被遗忘。
遗址下,两位学生模样的男孩在为清军是否勇敢抗击起了争论,我宁愿相信,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清军将士必定是人人奋勇的。对于这一点,博物馆里的文字介绍给出了中肯评价:临阵不惧,死战不退。
但在悬殊的力量对比面前,一腔孤勇只能沦为更大的牺牲。仅1860年的大沽口之战中,就牺牲了包括两任直隶提督史荣椿、乐善在内的众多高级将领,其余军士更不待言。在八里桥之战中,号称当时第一悍将的僧格林沁孤注一掷,企图用骑兵冲锋的战法破敌,不畏死的勇士们挥着马刀冲锋,最终为前所未见的密集火力击溃。据统计,清军阵亡3000人(一说1000余人),英法联军仅阵亡12人,战损比高达250∶1。其惨状,与六百五十年前野狐岭上的一幕何其相似。

大沽口”威“字炮台遗址 摄影 张佳
屡屡惨败,终于让紫禁城内的天朝大梦有所觉醒,旧日的长城已经崩塌,庙堂之上的有识之士决定师夷长技,中国近代化开始缓慢而艰难地启动,这又催生了后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将目光投向遗址的西南方——穿过滩涂和都市林立的高楼,25公里外的小站镇。就在大沽炮台被拆除五年前,另一个重要人物从那里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这个轮回的终结者。
历史的小站
从大沽炮台遗址到小站约需五十分钟车程。如果只看市容,这是北方城乡接合部再普通不过的小镇,沿街商铺是青砖仿古建筑,“岐口海鲜”的旗子迎风舒展。只有路牌上的街道和地名,提醒着人们这座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镇”那不平凡的过往:前营路、后营路、盛字营村……
考虑到大沽重要的战略位置,清廷在咸丰之后,加大了这里的军事力量存在,先后有淮军精锐盛字军、地方团练津胜营、新编定武军,最著名的当属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1895年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让迁延数十年之久的“师夷长技”宣告失败。海上长城尽毁,京城亟需新的拱卫力量,“小站练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同年12月,袁世凯在小站组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以组织严密、号令严明、装备精良著称,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除了军事上学习德、日,还要教授测绘、地理、外语等,一扫清朝旧式军队的暮气,可谓前所未有,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化陆军。清廷也将其依为干城。
伴随着新建陆军实力扩充,袁世凯逐渐走近权力核心,后因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于是将新建陆军统称北洋军,逐渐形成清末民初时期国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从这片军营里走出了4位总统、1位临时执政、9位北洋政府总理和34位督军,他们左右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长达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
昔日的荣光都湮没于岁月,后人在遗址上建成小站练兵园,复原了当时的城池、讲武堂等,讲武堂南门前悬挂着一副袁世凯所题对联: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敌视死如归。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练兵治军理念。
讽刺的是,他的新建陆军在庚子国难之际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八国联军经大沽口长驱直入,京城再次陷入浩劫。在小站期间,他先是出卖维新派,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被禁瀛台。又过了十多年,正是在他的“逼宫”之下,清帝宣告退位,一个轮回彻底结束。对外敌束手无策,对君主两度背叛,其“忠勇”由此可见一斑。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多年后,袁氏复辟称帝,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在国人唾骂中死去。北洋群龙无首,从小站出来的一众将领各自立起山头,中国遂陷入互相攻伐的割据时代。在漫长而无意义的混战中,以“新”著称的北洋军逐渐消磨掉锐气,由“新军”而军阀,最终被时代淘汰。

小站练兵园内 摄影 张佳
走出练兵园时,我长舒一口气,仿佛合上一本厚重的书,皇家行宫里的起落浮沉,海上要塞的落日硝烟,还有野狐岭上的朔风万里,一幕幕在眼前飘过。满人以前朝历史为教训,开国之初气象为之一新,但终究没能逃出“历史周期率”,并且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他们不断缝补,勉强度日,却亲手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历史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轮回罢了。
广场上正播放着李叔同作词的《送别》,在这意味悠长的旋律中,那些风云往事逐渐远去,天空云开雾散,阳光洒进大地。
张佳
杨嘉敏
结论慢慢地,他不仅陷入了沉睡,而且失去了知觉。
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