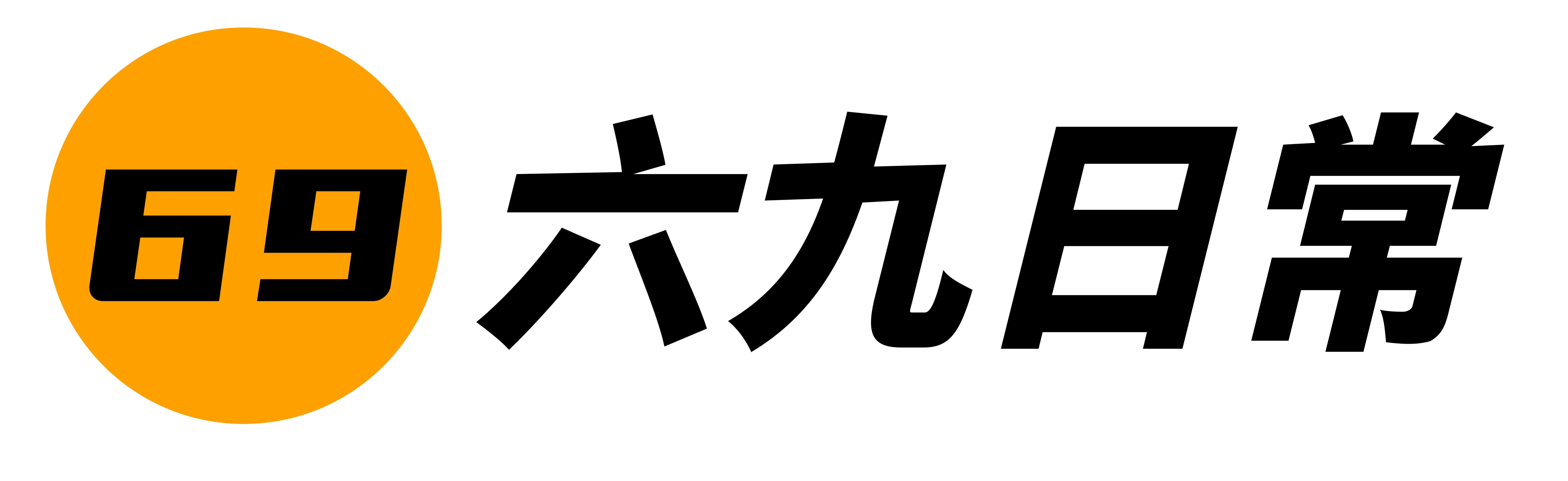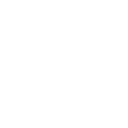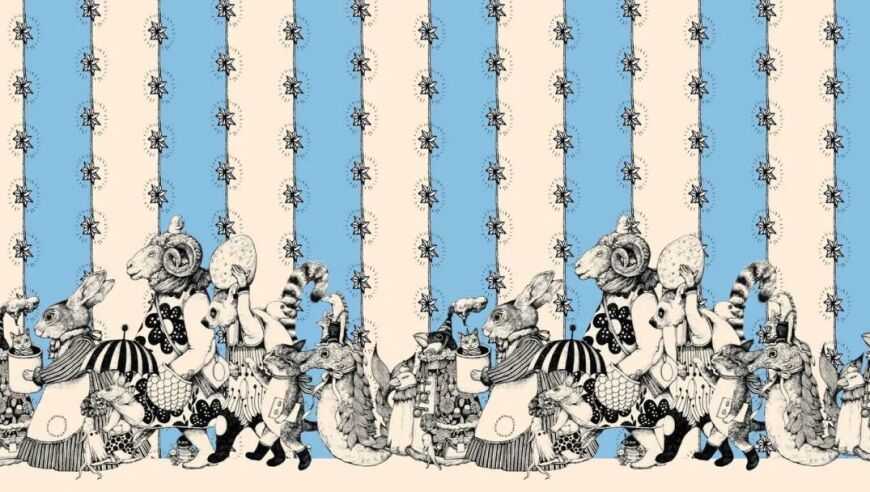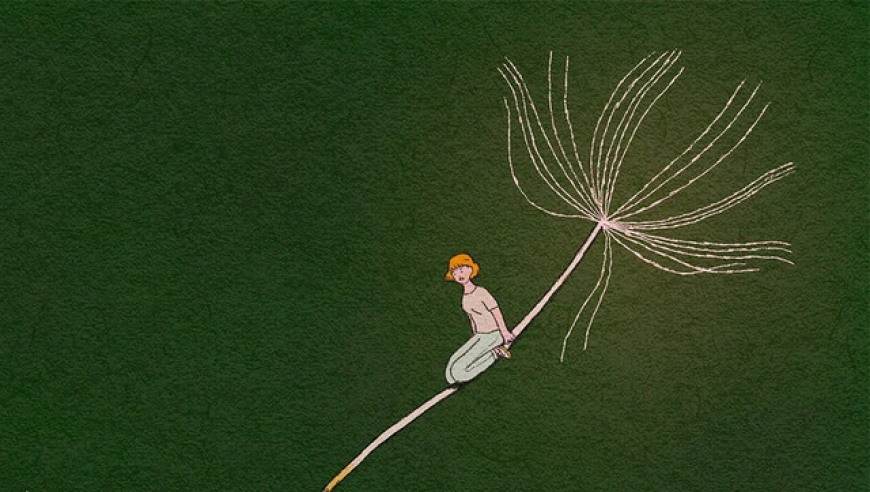2024年3月,广州,“捡来的博物馆”外墙贴满门牌。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过去很多年,“城中村艺术家”都是陈洲和妻子张晓静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自2007年底,夫妻二人开始在广州的城中村生活,不断穿梭于拆迁过程中的城中村,收集各式各样具有时代特征的“破烂”。直至2024年初,这些城中村的记忆碎片第一次被集中展览,他们为其取名为“捡来的博物馆”。
“捡来的博物馆”位于广州海珠区的怡乐社区内,是一处占地40余平米的平顶房,里面堆有老式摆钟、破碎的瓷器、大头贴等旧物。最显眼的是博物馆四周外墙贴满的铝制门牌,蓝色的,绿色的,密密麻麻,数量达2100多块。
博物馆开幕后的两月内,南方周末记者4次对话这对城中村艺术家。如今的他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家庭与其他艺术项目,褪去了些许年轻时对于“城中村艺术”的狂热,但那段岁月,对他们的影响一直都在。
以下由南方周末记者根据陈洲的讲述整理: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
博物馆展览开幕后几天,晓静的学生发来消息说,我们前一晚上热搜了。我们觉得很奇怪,我都多少年都没上微博了,爬起来看,有篇报道我们城中村博物馆的文章点击量有五六千万。没想到反响这么好,可见很多人对此是有共鸣的,或许跟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背景有关。
有哥们儿通过报道看到了我们做的东西,问我去到城中村怎么跟他们打交道的。我突然觉得很难回答,因为你会很难理解,我本来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
我1973年在安徽大别山区的一处农村出生。我们小时候,初中考高中非常难,一个班六七十个人中,也就两三个孩子能上高中,可以说95%的孩子都没有学上,就背井离乡,到处打工。我哥和我弟弟读到十几岁都辍学打工了。有一年,弟弟去沈阳打工,借点盘缠就上路了,等他回到家身上都长跳蚤了,我特别心酸,触动太深。
后来“打工潮”来临,想发展就得追求“打工和远方”,我那些同学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我母亲也出远门务工,有时一年只回一次家。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腊月天里,下雪天,我们就朝山顶上望,等她回家。我那时候就想,我绝对不能打工。
我太太家庭条件比我好,她在江苏的一个县城长大。我之前跟她开玩笑说,我要是没考上学,肯定也找不到她,可能就是一个整天在她家门口休息的工人。我有很多这种荒诞的想象。
我俩都是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去了法国留学,那个时候我们不想跟家里人要钱,留学的七年里,有六年都在做兼职。我在超市做过搬运工、开过货车,也当过洗碗工,我太太做服务员,我们都有一股“底层精神”。
所以城中村的老百姓,会让我想到自己和身边的人,说白了,相当于回家的感觉。回国后,我也可以不进城中村搞艺术创作,但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艺术要回到人民群众当中”。我就身在其中,城中村对我来讲,再熟悉不过了。

博物馆内景。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改革开放,南方经济活跃,广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跟城中村紧密相连,它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里面有消费和需求,大家可以在这里落脚、务工,迅速地更换工地,效率非常高,是一个可以靠自身运行良好的系统。我打个比方,广东像一个巨人,城中村就是他的胃,是一个城市提升发展的动力系统。
当然城中村确实有卫生方面的问题,但你不能否认它推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很多建设都是这些人来完成的,它有它存在的价值,是这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站在外来劳工的视角看,很多人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是几十年的努力都贡献给这座城市。
我也做过两年老师,一下班就跑进城中村,那时候经济也好,我也觉得当代艺术我一定能做好,我们到处串村子做方案,因为我视野已经开阔了,我也不觉得自己会掉到深渊。后面我辞职了,专心去做城中村艺术。
“这里有一个田野”
我们认识广东就是从一个拆迁村开始的,广州美院大学城附近有四个原生态的村落。我连天河都不知道怎么进来,直接是从法国巴黎飞到广州的大学城,住到村里面了。
2007年元旦,我俩刚回国,她去美院教课,我每天没事就在附近的村里溜达,感觉特别新鲜。我们首先被大学城遗留的一些村落吸引,它有传统的格局和建筑,比方说水磨砖、宗祠,还有石板街。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别让我们很震撼,因为在北方看不到。
你能感受到南方的城中村,有南方水乡的感觉。到处都有船,作为一种公交系统把大家串联起来,卖菜摊都是四面八方来的,大榕树根有村民悠闲地抠脚丫子,很有生活气息。
在这里,我惊讶地发现,有老头把金山箱劈柴用来烧水,金山箱是老一辈人当年去美洲打工时制作的特制皮箱,村民他不当回事。我赶紧去找,结果已经烧完了。他们把很漂亮的漆器扔掉,包括雕花工艺非常棒的米斗,在我看来,都是可以放进博物馆的水平。
看他们把一些物件扔出来,我觉得好可惜,也意识到这里有一个田野。我受过一些比较好的当代艺术的训练,中国又是一个乡土社会,我目睹了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么急剧的口上,有些事一定值得去做。
2009年,我们的媒体朋友说,“林和要拆了,你们艺术家肯定会很感兴趣”,我们就去了。
林和是最典型的一个城中村,坐落在火车东站对面,很多外来人口一下车就直接到这个村子落脚。里面握手楼非常多,黑乎乎的,白天都开着15瓦的老灯泡,那种景象我们从没见过的,都不敢进去。
我们在林和,有一个青岛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大姐送给我们一面小铜镜。她是1990年代的大学生,有“下海”的梦想,想来南方追求飞黄腾达的新生活。这面小铜镜是她出发前,妈妈送给她的,女孩爱漂亮,在路上梳妆用。
我们只是偶尔相遇,她就把她南下务工的故事讲给我听。她从一个大学生,到两个孩子的妈妈,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个村子里度过。虽然她最后只是在城中村开了两家卖女性用品的小档口,卖袜子、胸罩、化妆品,生活了一二十年,一直不太好意思回老家,但她并不遗憾这段南下的经历。
我后来还在城中村碰到一个江西老表,他开一间小杂货店,卖音响、电视机和床,就这样生活了20年,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碰到拆迁,他说,“我回家都不知道怎么种田”。他走的时候,在一个音响壳子上写,“希望广州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

江西老表在音响上的留言。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继林和之后,我们再到杨箕。那时正值房地产热,拆迁都交给开发商负责,时间紧,效率高。你现在看到的杨箕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外墙呈环形,有几个门可以进出,里面人口密度大,有传统的祠堂和石板路,报社的工作人员晚上下班经常去里面吃大排档。
我们有17米长的一个孩子的奖状拼贴图,主要是一个叫徐小惠的女孩的,每一张都很完整。她在杨箕村得到很好的成长,成绩优秀,从小到大都有奖状。拆迁以后她就回老家了,很可惜。像这样的流动儿童,城中村有许多。
我还在杨箕村捡到一只可爱的小灰熊玩偶,应该是小孩子的玩具,它压着一个没写完的作业本,放在桌上。小熊身下有个开关,一扭就能放出音乐,声音很美。我经常把音乐打开,陷入沉思,我会想到,小孩子肯定是边写作业边玩这个小熊,那应该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后来玩具被扭坏了,那张桌子我也扛回去了,那是用一种很传统的木头做的,很厚实。我给刷上蓝漆,现在我儿子女儿经常在上面画画,写作业。
“故乡的路没了”
目前博物馆外墙的门牌是2100多块,实际上我们收集的门牌有7000多块。门牌收多了,我儿子都以为门牌是我们的专利,他在街道上见到门牌,就问是不是我们家的。
其实收门牌的想法,不是我们进城中村第一天就有的,而是一趟、两趟、三四趟慢慢形成的。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想收,只是去看看村子怎么消失,后来觉得这些街道名字是有价值的。
这种价值体现在它有悠久的历史。很多地名我都很喜欢,比如琶洲的官禄巷、占决大街、艳龙里、玉龙里、潜龙里等等,冼村有一条七龙大街,听起来火力好猛,还有接云大街、择邻里,都是很浪漫的名字,都不在了,我们故乡的路没了。
地名里,有的就是古汉语和方言沿袭下来,带有美好的寓意,很多都跟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有关。我频繁去城中村“捡破烂”那几年,中国当时还没有地名保护政策,开发商拆了就可以随便起名,罗马家园、御花园、带有“皇家”字眼等乱七八糟的名字就冒出来了。
我们最开始收集的门牌,是白底红字的“出租屋”塑料牌。以前,外来人口住的地方都要挂牌,这些门牌是一个时期城市发展的见证,我不希望它们就这么被挖掘机埋了。

2010年,陈洲在林和回收门牌。受访者供图
2010年,我在林和村举一个牌子,上面写“高价回收城中村门牌”。10块钱一个。实际上,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些路名是有意义的,一旦拆了就没了。比方说你只知道杨箕村,但是你不知道杨箕村里面有潜龙里、择邻里、仁善里、仁和大街这样丰富的名字,挺遗憾的。有统计显示,仅仅是1991年至2000年,广州老地名就消失了1031个。
有警察说我扰乱社会治安,我说我在做文化保育,警察听了也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后来就把收缴的门牌都给我了,我们处成了朋友。
有一年,我们在深圳9号线地铁的香梅站,做一个门牌展览项目,收集了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块门牌,贴在一面13米长、3米3高的墙上,主题就叫“故乡”。当时有个男人盯着这面墙看好长时间,老不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上面有个上海的门牌叫“杨树浦路176号”,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后来拆掉了。
这些年,我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城中村,至少得10个,收集了很多东西,一直在广州美院沉积。我就想,如果有一个博物馆,让我把我所遇到的人和故事都展示出来多好。我甚至想去买一栋小房子,做真正的博物馆,但和太太商量后,觉得这会影响家庭开支,不现实。
这么多年一直对博物馆耿耿于怀,去年突然有个机会展览,我也蠢蠢欲动。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在做社区共建项目,希望社区有活力,我们的理念和项目刚好符合,彼此付出的代价都很小。对我来讲,他们支持每月近5000元的房租,我也不需要再专门买房子展览。

2024年3月,广州,博物馆设在社区内。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城中村的两种时代
那些拆迁过的村子,我从来不去看,都成了新建小区,跟我们普通社区没什么区别,也没有必要去。
几年前,我坐有轨电车到琶洲,看到以前的祠堂变成了售楼部,进去问了一下房价,已经涨到4万多了,我整个人就眩晕在这种时空交错中了。太贵了,买不起。
黄埔区有个叫笔村的地方,朱熹的后人迁徙过来,在那住了六百年。2019年国庆,笔村正在搞拆迁,做棚户改造。我就带女儿去村里面,看大榕树、池塘和宗祠,也去看了上珍家塾,那是乾隆年间的私塾。我知道,以后这些非常传统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我希望女儿能对城中村的这些环境有个认识。这就像传承一样,我从乡村出来,上学进入到城市里面,我不觉得城市里的东西有多难理解,反倒是村子里一些传统古典的文化比较珍贵。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觉得农村跟他们很遥远。
现在,我儿子5岁,女儿也10岁了。说实话,在有孩子之前,或者说孩子更小一点的时候,我整天从高校下班以后钻进城中村里,不能赚钱,一心搞艺术。但钱很重要,家庭也很重要,后来我开始创业,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再投入到城中村艺术了,而且现在时代背景也不一样了。
在深圳地铁站展览时,陈洲父女合照。受访者供图
在我看来,城中村经历了两种时代。以前是市场经济推动房地产主导的城中村拆迁改建的时代,地产经济疯狂生长,没有文化保育概念。现在城中村的建设和推动由政府主导,市场需求没那么大了,政府在保护故乡的路等方面谨慎很多,会考虑发展的需要和消化能力。
所以是有个分水岭的。我个人觉得,房地产经济增长的时期,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如何规划、建设街区,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传统文化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被破坏。我现在展览的那些旧物,实际上属于过去那个时代。对于当前这个时代,我已经没有很强的动力投入精力了。
但我们还在关注城中村。2023年底,以广州制衣行业供销地闻名的康乐村拆迁,工业布料整车整车拉到深圳,用来做拖把和擦墙布。两毛钱一斤,好便宜,我们就去买了一些好看的碎布料。今年是龙年,我们带着孩子和街道的居民,一起用这些布做了一条龙,挂在博物馆里。
还有村里面的人在拆迁前送东西过来,比如塘下村的村民搬走了,他们就把财神爷送给我,挺有意思的,这个馆现在变成一个互动馆了。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没有什么力量,就是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发出这样的声音,承认城中村的价值。那些过去的日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可以遇到那么多人,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由什么样的人群组成的,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座城市。我相信,这些都是能产生共鸣的。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柯愉乐
谭畅
结论: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中村”的价值和影响,并积极寻求将其纳入艺术创作和社会发展的议题。许多艺术家如陈洲和妻子张晓静投身城中村艺术创作,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成为了这一群体独特的标志。
“捡来的博物馆”作为第一个“城中村艺术”的展览项目,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这个时代的背景与以前大相径庭,但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许多因素仍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人口密度高、商业需求强烈等因素使得城市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卫生和历史遗迹的丧失。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也在采取措施保护和修复历史文化遗迹,避免类似的现象再次发生。尽管艺术创作和个人努力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艺术家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希望通过博物馆的方式将城中村的故事和经验呈现出来,引导公众思考城市的社会发展。
此外,社会责任感在当代社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本次展览中,陈洲和妻子的作品中体现了他们的实际行动,即鼓励和支持本地年轻人投身基层工作,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这表明在新时代,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如何让城市更好地融入人民生活,将成为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捡来的博物馆”和广州城中村的艺术展揭示了现代城市进程中的新机遇和挑战,提醒我们要尊重和珍惜过去的城市历史,同时也要适应和参与到未来的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