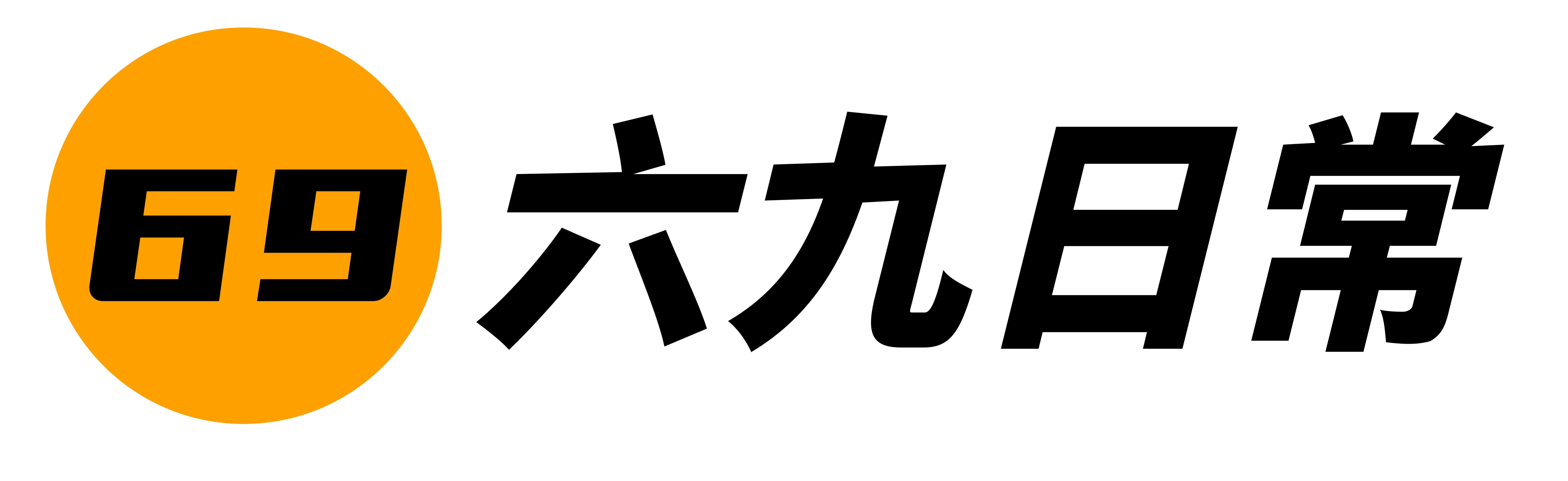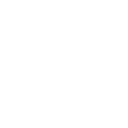◎唐山
“现代英国法律的历史就是一部由一个人的思想所引发而发生彻底变革的历史。”这是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对杰里米·边沁的评价。
很难找到一位思想家,像边沁这样,被贴满负面标签:他开创的功利主义被视为“庸俗、狭隘、自私、冷漠”,成了“利己主义”“极端自私”的代名词;一代文豪狄更斯曾写小说讽刺边沁……
然而,建立国家教育制度,改革济贫法,婚姻登记,发明家保护,不动产登记,公共卫生立法,废除流放罪,改善监狱,刑法改革,证据法改革,废除宗教考试,改革陪审团制度,人口普查,兵役登记制度,放弃殖民地……边沁在世时,对英国政治影响有限;他去世后,英国几乎所有政治变革都来自边沁的思想——他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至今仍在驱动社会的自我变革。
梁启超曾说:“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错过边沁,可能是传统中国在近代化转型中的最大遗憾。回望来时路,不能不惊叹于边沁那超凡的智慧与胸怀,亦为前贤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而扼腕。
学者李青的这本《功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道尽其中委曲。
不快乐的孩子创建了“快乐为本”的思想大厦
1748年2月,边沁生于伦敦的一个律师家庭中。因爷爷、父亲留下巨额遗产,边沁终生衣食无忧。
3岁起,边沁便开始学习拉丁文。梁启超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中称:“幼而颖悟,好谈玄理,心醉典籍。5岁,家人戏呼为哲学儿,年14入牛津,崭然显头角。1763年,入林肯法学院,学法律。及法国大革命起,曾三度游巴黎,察其情状,经验益多。”
然而,边沁并不快乐。
边沁从小对鬼魂非常恐惧,这种恐惧源自他的想象。边沁知道,这些恐惧并无现实的基础,可只要在黑暗的房间中,他就会害怕。从孩提起,边沁就在思考“真实”和“想象”之间的冲突。
从中学到大学,边沁过得都不愉快。因身材矮小,边沁的一个大学同学常恶作剧式地抓住他的双脚,让他脑袋朝下,悬在半空。边沁说:“在牛津,有些人放荡奢靡,有些人抑郁乖僻,大多数人则是毫无生气的。”他声称,在牛津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恐怕没有谁比他更不喜欢牛津的了。
不快乐的边沁,却创出以快乐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简言之,就是立法应以“增大社会全体的快乐,建设社会全体的痛苦”为基本原则。
边沁这么说,也这么干。晚年因病垂危,他对友人说:“所有的青年人都走开……只要你一个人看着我。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痛苦尽可能减少到最小限度。”
边沁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深感骄傲,他说:“爱尔维修(伟大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之于道德界,正如培根之于自然界。因此,道德界已有了它的培根,但是其牛顿尚待来临。”言外之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会一统道德界的江湖,彻底解决种种争议,使道德真正落地。
与其争论道德法则不如为幸福讨价还价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价值在于:此前道德争论多基于虚构的前提,而这种架空讨论永无结果。以“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为例,各方都拿不出足够证据,越争论,越坚信自己的立场。争论并没强化共识,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
边沁则绕过这些暗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言自明,立场不同,并不影响讨价还价,在此层面争论,所有人都是受益者。
于是,边沁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批评。
卢梭认为,个体要生存,就要组织起来,形成共同体;共同体与个体之间靠契约维系。只有人人既承担义务,又享受权利,且彼此对等,才是合法而理性的契约。好社会应致力于制定好这个契约。
此论逻辑严整,却充满想当然。只有确信个体会自觉遵守契约,违反契约的惩罚足够有效,它才能有效运转。但人真的是“契约动物”吗?边沁不客气地指出:“我与原始契约告别了;我把它留给那些以这种喋喋不休的话来自娱的人。那些人会觉得他们需要它。”
边沁认为,与“契约动物”相比,人更像“利益动物”。与其沉浸在自然法则、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主权、积极自由等“人造大词”中,不如回归本质——服从并非人的天性,需后天习得;逐利则与生俱来,先天就会。既然“杀头的事有人做,赔钱的事没人做”,那么,法律应顺势而为。
边沁特别不喜欢卢梭虚构的共同体。他表示:“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于是,边沁与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主义走到了一起,他们都相信,在法律的正确引导下,“个体的恶可以转化为公共善”。
抹去了“粗俗”却也阉割了革命性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给变革现实以抓手。
此前,“爱国”“尊重传统”“一直如此”“帝国利益”“法律变得太多太快,不利于执行”“治乱世,用重典”“花钱太多,看不到收益,没必要搞”“不求走得快,但愿走得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都是拒绝变革的借口。其根本在于,总有人希望维系传统的政治依附关系,拒绝将其转化为利益关系——因为后者会让利益的来源清晰化,前者却能浑水摸鱼。他们不敢明着反对用自由竞争秩序替代等级秩序,用社会原则替代政治原则,就制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进行模糊处理。
边沁则让讨论变得直观,甚至可量化为具体数字,让每个理性的人都能作出正确选择。
戴雪曾赞美说:“他(指边沁)说服了他那一代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说服了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相信,为了公共福祉,人们是可以在明确的原则基础上,对法律进行系统性改革的。”
然而,边沁的理论大厦也有一个死角,即:幸福无法量化。所以边沁认为“快乐多、不快少”就是幸福、认为快乐可以计量等反而将自己带入困局:吸毒也让人快乐,则鼓励吸毒就是正当的?边沁的哲学一度被嘲为“猪的哲学”。
边沁产生这样的偏执,因为他是一个对人性充满信心的人。哲学家蒙塔古说:“边沁易动恻隐之心,乐于扶危济困。无论任何事物,只要边沁认为有利于造福人类,他就会非常关注;从事改革事业,既未给他带来金钱,也未给他带来高位,反而使他屡受讥讽,甚至辱骂,但他仍然为改革事业长期辛苦劳累;由此可见他对人类存心之仁厚。”
边沁醉心哲学,写作拗口,被称为“现代梵文”。这也给人们误解他提供了可能。
边沁之后,穆勒加以修正,以“幸福”替代“快乐”。这使功利主义理论不再“粗俗”,却也消磨了边沁理论的锋芒,主动迎合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经济发展有利社会进步。
功利主义为何在东亚被污名化
明治维新中后期,功利主义被译介到日本,但从一开始,便以穆勒的修正版为主,较少提及边沁的基础版。原因有三:
其一,此时日本社会中曾遭打压的保守势力回归,以“追寻日本自性”“弘扬日本传统文化”等为借口,对西方思想加以想当然的、任性的批判,功利主义恰好撞上逆风。
其二,日本在迅速崛起中,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易与穆勒版产生共鸣。
其三,日本崛起是为了“富国强兵”,边沁重视个人利益,对缺乏相关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感到难以理解。
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称:“功利主义作为国家经济主义一直是好的。但若将之作为关系个人唯一的道德主义则是不行的。”
边沁强调的明明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尊重“个体利益”,也是为了“共同体利益”。但日本学者本能地担心,关注“个体利益”,会不会引发混乱?会不会失控?连福泽谕吉也表示:“现今社会的变迁太过急激,而且西洋诸国的学说教义等东渐以来,人们大都多歧亡羊。”
更麻烦的是,不同思想竞逐,渐生派系之争。传统派为污名化西洋派,匆匆将边沁的学说定名为“功利主义”,从而将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辨”植入其中,附以批判的意味。可不论是边沁,还是穆勒,都反对将私利置于公义之上。
通过日本转译,功利主义传入中国。梁启超先生初期译成相对公允的“乐利主义”,并且注意到了边沁。但在时代压力面前,梁启超等人也无暇深入研究。到后来,更是直接袭用“功利主义”这一污名化的译法,并照搬日本人作出的误断,致功利主义在中国始终以穆勒版为主,致边沁很少被人关注到,致功利主义蕴含的革命性、可操作性、实践理性等因素被长期尘埋。即使卢梭式的浪漫想象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仍无人注意,早在200多年前,边沁曾怎样睿智地直指其妄。
时光流逝,检验着思想的穿透力。《功利主义》是一本体量不大的小书,却让人“一篇读罢头飞雪”,万千感慨,尽在其中。
结论,